提起骆以军,我会想到雾气氤氲的街头巷尾,衣着暴露的站街女在忽明忽暗的霓虹招牌下用力吸完最后一口香烟,身边的违建楼里缠满了蛛网,蛛网上挂着几只奋力挣扎过的尸体。烟火气、市井味儿、世间阳光难照到的地方,都在骆以军的故事里鲜活而蛮横地生长着。
当然不止如此,他的小说被梁文道夸成“在整个当今我所知道的文坛是最特别的”。台湾作家陈雪评价他的新书《匡超人》——“在每一个故事之间,埋藏了机关、典故、隐喻,他建构了可以层层打开、不断翻覆的结构”,他细腻而深入地采集研究着属于台北、也属于世界的城市人类学。
比如他写一对生得标致却活得孤独的私生子,“他们像失聪的鸟,线条柔和,却不知道是什么部分和这世界格格不入。”
他写与咖啡屋女主人的宠物狗相处,“在这个明净爽飒的初冬午后,确实让我昏困地感受到一种极接近‘爱’的寂寞情绪。”
如今我们草草码个朋友圈就完事儿的素材,他用最擅长的文字一针一线编织成了动人而真实的故事。

骆以军,台湾作家,代表作《西夏旅馆》、《我们自夜暗的酒馆离开》。
香港书展分享主题:一件很小很美的事,图源网络
扒着生活的缝儿,竖耳听故事
骆以军在香港书展分享现场为我们带来了五个故事,其中三个小的关于粉红按摩店的美少女:
故事一号的主人公曾经是女排球手,在高强度非人性化的训练下把膝盖折腾坏了,如今她穿着太空裙、高跟鞋,用这双腿为客人踩背,“像是从川端康成小说里跑出来的睡美人,又像一只蝴蝶或是小鸟,在我背上跳芭蕾”;
二号姑娘曾经与爷爷住在花莲乡下相依为命,去学校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某天回到家发现爷爷去世,爸妈匆匆回家却没把她带走,“非常村上春树的孤独:这个宇宙不需要其他人,就只有一个末日之间,一个人在其中这样活着没有快乐,也没有哀伤”;
最后这位女孩体型较为健硕,在台南乡下长大,整日挖土豆挖地瓜,能够辨识各种昆虫变化的模样,当她再走高速经过曾经的家时,尽管早已物是人非,她却能立刻认出那棵非常高大的陪自己成长的树,与她的家。
“这些都是草率的故事,不是小说。如今人与人可能只有在消费性行为中,才能听到一段不一样的故事。”
有人说骆以军是为了写作而生活,这话不假。不仅是小说,他还写固定专栏,既非社论也非书评,而是每周按时端上一个热腾腾的故事,如此往复整整十年。骆以军说自己的人生经验并不丰富,追到现在的太太、结婚生子、养家糊口,只有学生时期的混混打架经历有许多故事可说,但写了一两年后也就枯竭了。
他只得潜入生活角落偷听故事,来应付写作上不断被掏空的感觉——这种掏空感,在他写完《西夏旅馆》之后尤为明显,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想再写长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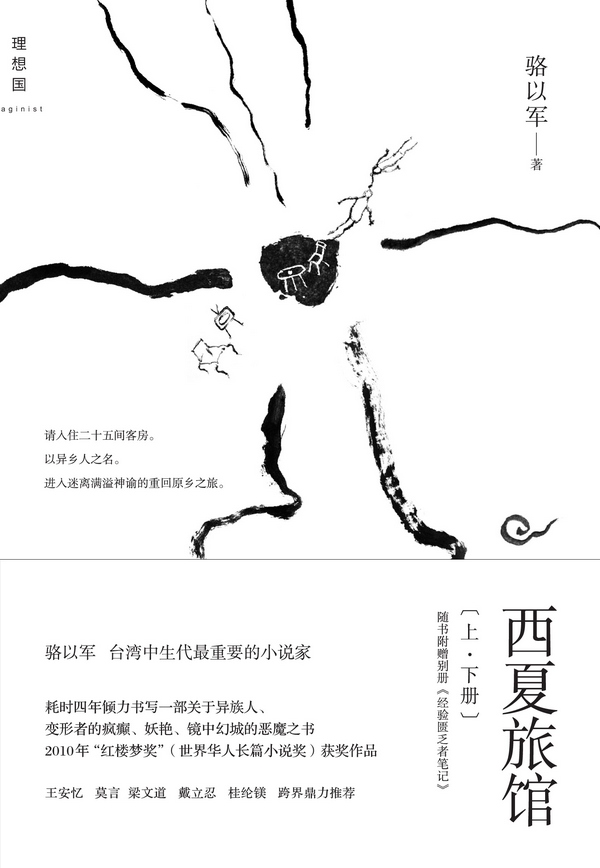
诉尽异乡人离散与追寻的《西夏旅馆》,图源网络
“在听故事的时候,你会愿意去尊重对方身后你所不知的苦难,或说变得比较谦逊,你会试图不羞辱对方,不把过大的标签贴在对方身上。”
在他眼里,故事不仅仅是灵感来源,它们更是一种生命经历,来扩充你本身受限的生活范围。这并不是一个对诉说者下定义、生看法的过程,听这些故事也未必能解决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悲剧或是历史上的伤痕。可是至少聆听故事这个时刻,应该存在。“故事就像安康鱼头顶的小微光,当你愿意说故事给对方听、或是你愿意听对方故事的时候,这个微光就会亮起来。”
于是他在咖啡屋一边动笔一边偷听隔壁桌相亲时聊些什么话题,在计程车上同司机讲载过的酒醉客人全都记不得家在哪,在香港老式按摩店听上了年纪的阿姨回忆小时候在东北家乡溜得一手好冰、在小酒馆里听哥们儿说自己的一夜情与性冒险然后流口水……城市无传奇,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光怪陆离,你来不及听到更多背景。他就像一只捞采浮游生物的虾子,一个在外太空飘行的怪兽,捕掠着各种光影与他人的梦。

图源网络
正如汪曾祺在《说短》中写道,“以前人读小说是想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生活,或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生活。……现代读者要求的是真实,想读的是生活,生活本身。”骆以军的小说操着股浓厚的魔幻现实味儿,他从不写惯性思维中的圆圆满满,也不刻意营造事故以突出作品的戏剧感,而是把放大镜对准了人类种种病态关系中的疏离、猜忌与冷漠,并试图强调当前这个因科技发展、因消费主义、因流行文化而形成的畸形苦难众生相。其中没有什么傲人的大道理,他只满足于说好一个故事,并击中你最后一块软肋。
为了成熟叙事,他这十年来一直坚持着素描练习,重复写一个场景,把它写深、写活。如日本小说家村上龙的作品《到处存在的场所到处不存在的我》里描绘的那样,人类几乎就像是变形的讯号——幼儿园的妈妈全在勾心斗角,表面上赞美对方,其实都在替自己儿子挑选未来媳妇。现在的人啊,也越来越难概括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骆以军《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图源网络
“大家看我的《西夏旅馆》或是其他作品,会以为我有丰富的猎艳经验,其实不然,我只是有很强大的COPY写轮眼,说不定你们就到我下一篇小说里了。”
他的写轮眼(漫画《火影忍者》中的一种瞳术)就这样无时无刻都在收发着信号,周遭的事物被筛选组织,而后变成故事。他将写作视为极限运动,而优秀的小说就是在萃取其中的神之光,残酷而变态。
为什么说《红楼梦》伟大得不得了?曹雪芹一定是个精神敏感的人,他一边要顾着和场子里的人瞎扯淡一边要当个搜寻器接收有用的讯息。打个比方,你走进青楼里开启雷达,要注意这些姑娘跟姐妹们在做什么,要留心她与她的男人在演怎样一出戏,要观察这个妈妈的行为举止,还要偷听来这儿的男人们都在谈些什么事情……这些讯息量的判读十分复杂,骆以军坦言要换作是他,这么折腾一个晚上就爆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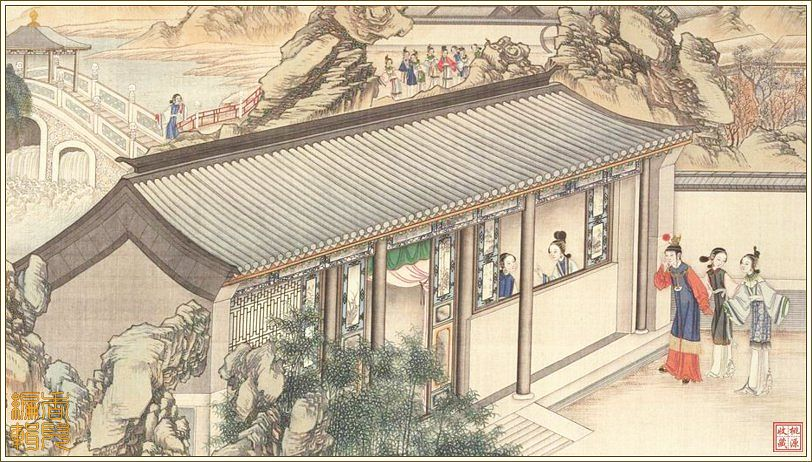
红楼梦大观园,图源网络
“我们二十多岁就进入到这一套西方现代小说系统,很用功地读卡夫卡、杜拉斯、福克纳,读拉美小说。这些人把自己当成二十世纪的天线,把人类所有的恐怖与噩梦用小说装起来,像削铅笔一样,尖锐地在削自己。”
他已经不想让五十岁的自己再这么敏锐。写得太用力的人,最后都疯了。
阅读影响你生命的厚度
阅读有多重要?读好读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个人的眼界与气质。
我不喜与时刻掉着书袋的人聊天,但骆以军不一样。他虽是个不管在交谈、分享、或是作品里都不自觉援引喜欢的文学电影进行例证的人,但能深切地感觉到,这些前人的智慧,是长在他生命里的。他也曾坦言,张大春是他的启蒙,也许过个十年,自己会全盘走进古典世界里,“展开一场旷日废时的行销。”
“如果在二十来岁读的是《哈利波特》,那想象中生命的可能性是很单纯很简单的。若在年轻的时候就花功夫好好读张爱玲、波拉尼奥、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对生活的整套捕捞搜寻体系会变得非常复杂。你会发现其实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存在状态,而不该因为一些很简单的故事变成圆圆的、短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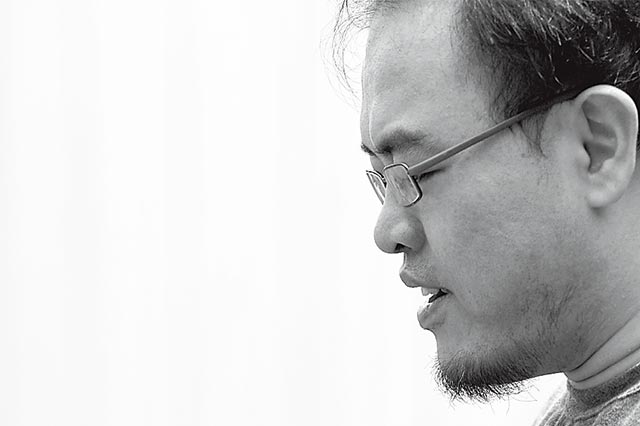
图源网络
这位作家喜用长句,却不难读,遣词造句之间挥散着西方文学翻译腔的味道,台湾调子中掺杂着一丝不太地道的东北味儿,偶尔夹带两句即兴粗口,挺有意思。这与他的生活环境与阅读经验不无关系。
他大学的时候,出版社出了许多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芥川龙之介、张爱玲,随着台湾解严,大陆的作品也一涌而进,可谓文学大爆炸。那个年代没有网络,学校又在山上,他就猫在宿舍里读加缪。可是吧,他很认真地念了三个小时,完全不知道书上在说什么,就睡着了,醒来发现书上都是口水。原来自己是个过动儿,无法集中注意力。于是每次翻开书就把纸放在一边,开始抄。这个过程,让他放慢了阅读的速度,也开始看懂了字串形成的句义。这一抄抄了二十年,吸收进大脑的文字,成了如今笔尖顺畅流出的词句。
“我没有写不出来的时候。”他说。
这个时代的挑战:活下去,别崩溃
如今的骆以军仍然习惯手写,坐在街边开敞着的咖啡屋露天座,点根烟抽一抽,脑海中大概有个景象就开始动笔。虽然这个时代变得很怪,人们没法承受庞大的信息量,都“砰砰砰”成了细胞原子态。
在这个信息快餐时代的大背景下,他也开始笨拙地玩起智能手机,用手指慢吞吞地拼出一字一句,再传上社交平台——哎,这十分钟编辑的东西,比花了十年写出来的还受欢迎、还多人看。
2013年,他开始在脸书上写家庭日常、生活琐碎,比如谁又在家门口春联上添了脏话、小儿子转头问他最近走红的《山海》歌词是啥意思、或是直接熬一盅浓稠鸡汤慰藉迷失在感情路上的年轻人……但他说呀,这堆东西到最后都没有意义,“花了很大心力去盖的建筑物,过了百年它看起来就是那么屌,可是如果在当时赶流行乱盖盖,最后它没超过十年就烂掉了。”

骆以军facebook贴文之“谁动了我家的春联”

骆以军脸书贴文结集跨界升级动画《小儿子》,图源网络
他还爱看抖音上的美少女跳着各种不可思议的舞步,可是经过每天一两个小时、连续十天的追踪以后,他觉得忧郁。这些主播在第一百支视频后,放的歌全部重复了——没有前人经验能够告诉你,生活在2018年的人类怎么能够活下去而不崩溃,怎么能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避免变成单细胞生物而后崩解。
“我外婆活到九十岁,她记得的重大事件顶多二十件。”可是现在的各位,面临着每个事件的窗被无止境地一开再开:泰国小孩洞穴被困,你要关心;黑镜到底是真是假,你要关心;中国好声音有没有作弊,你也要关心……人们为此感到同情、悲悯、愤怒,难道不该在这个当下有如此心情吗?也该。可这一切也全都朝着一个方向去了。
“现在年轻一辈的创作者比老一辈不幸,但也更坚强。”
后记
骆以军这两年迷上了寿山石,他说自己在此之前就是个运动员——训练、写作、阅读、赚钱养家,不懂生活,也没觉得啥有意思。
最近他在采访中被问到想要的父亲节礼物,脱口而出:“一块寿山石”。
于是被网友亲切调侃:真的不是瘦三十吗?
骆以军就像是隔壁家的叔叔,品味独特、满腹经纶,却把自己埋进生活,用文字与叙事奋力地把他成长的这片土地扒得精光,裸露出城市的命脉,再往里头注射进温柔与爱。如果想了解最道地的台北,你可得好好瞧瞧他笔下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