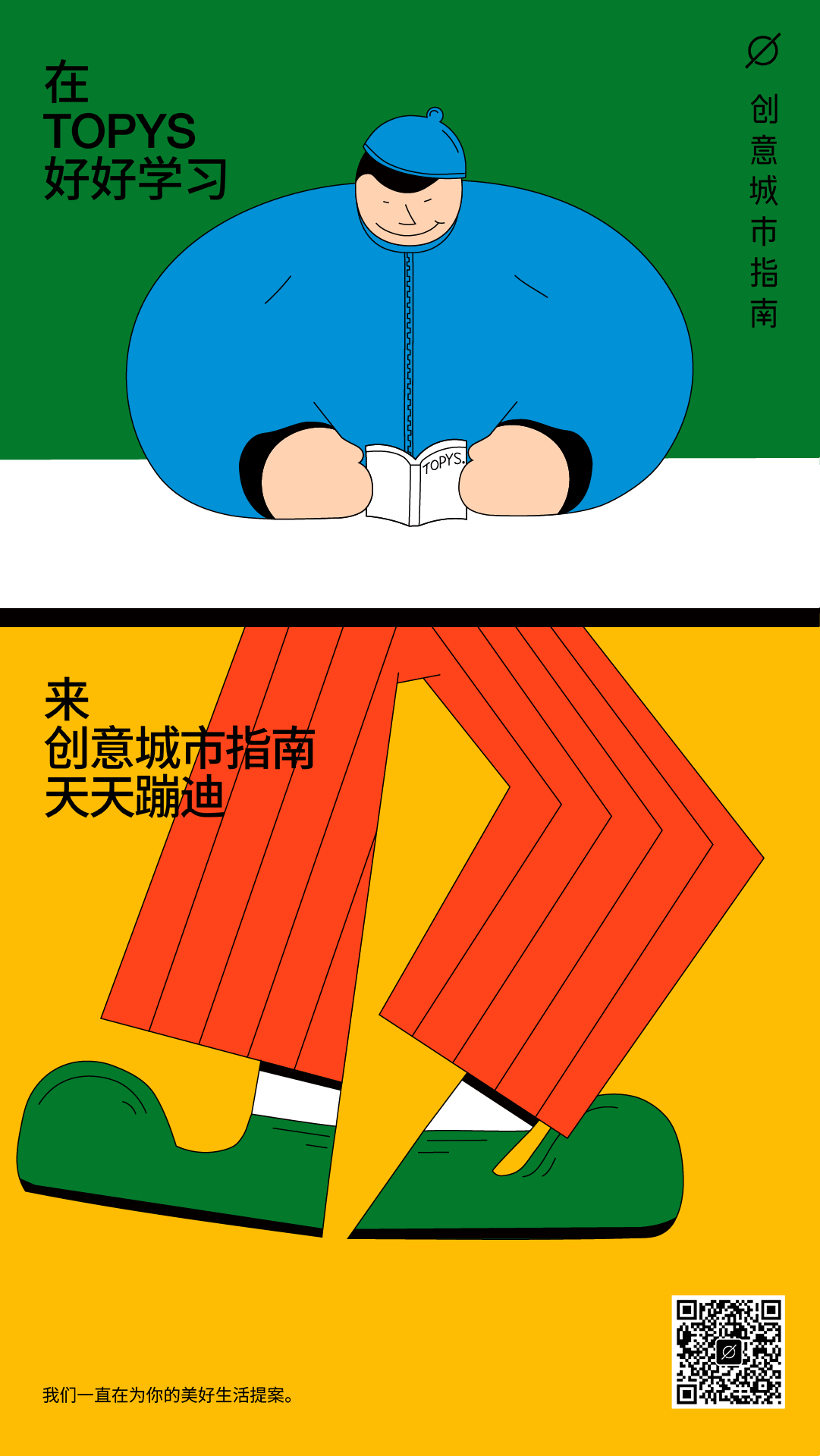就算你不记得Tango这个名字,也一定曾被他的画作逗乐过。
他擅长用黑白线条最简单地将日常感动他的鸡毛蒜皮戏剧化,生活中常见的图形与意象在他的画里,从来不屑待在你我默认的位置上。2010年起,因与朋友打赌,Tango开始进行“一日一画”计划,下班回到家抽出半小时完成画作,“三幅能够画完的,就不画第四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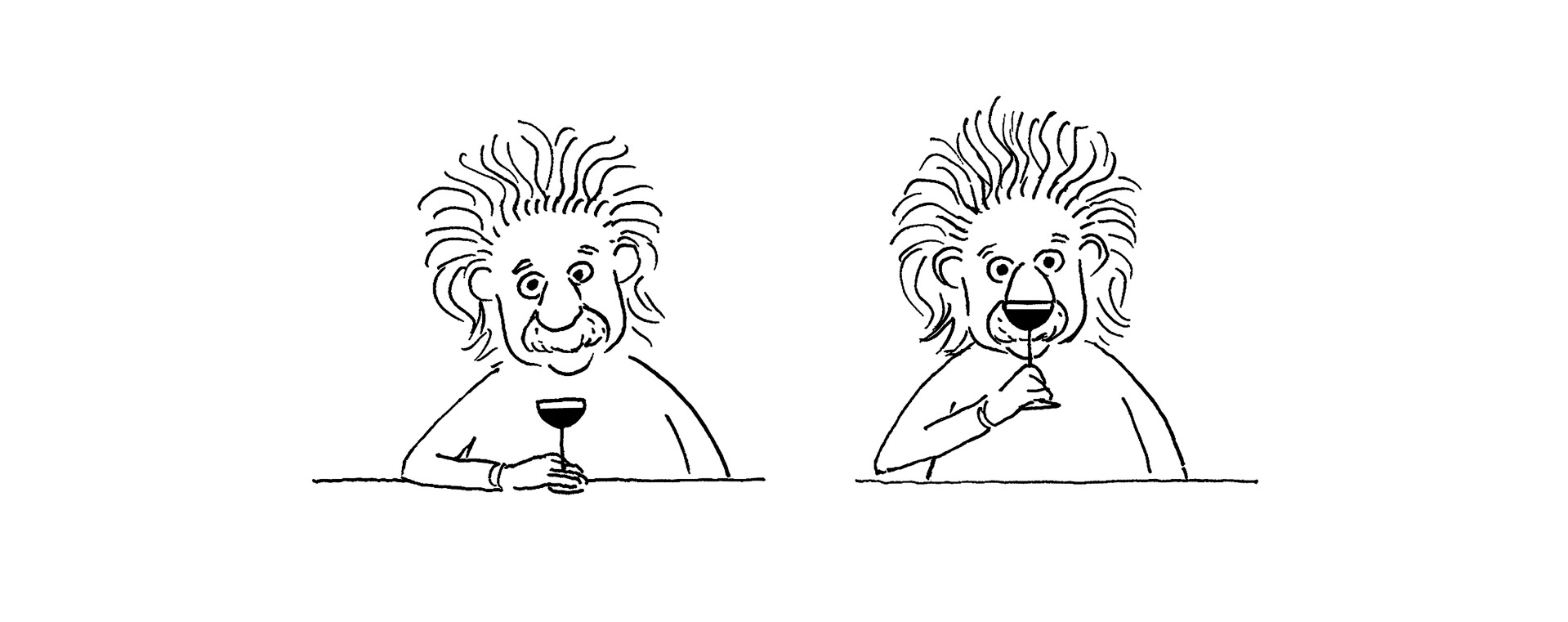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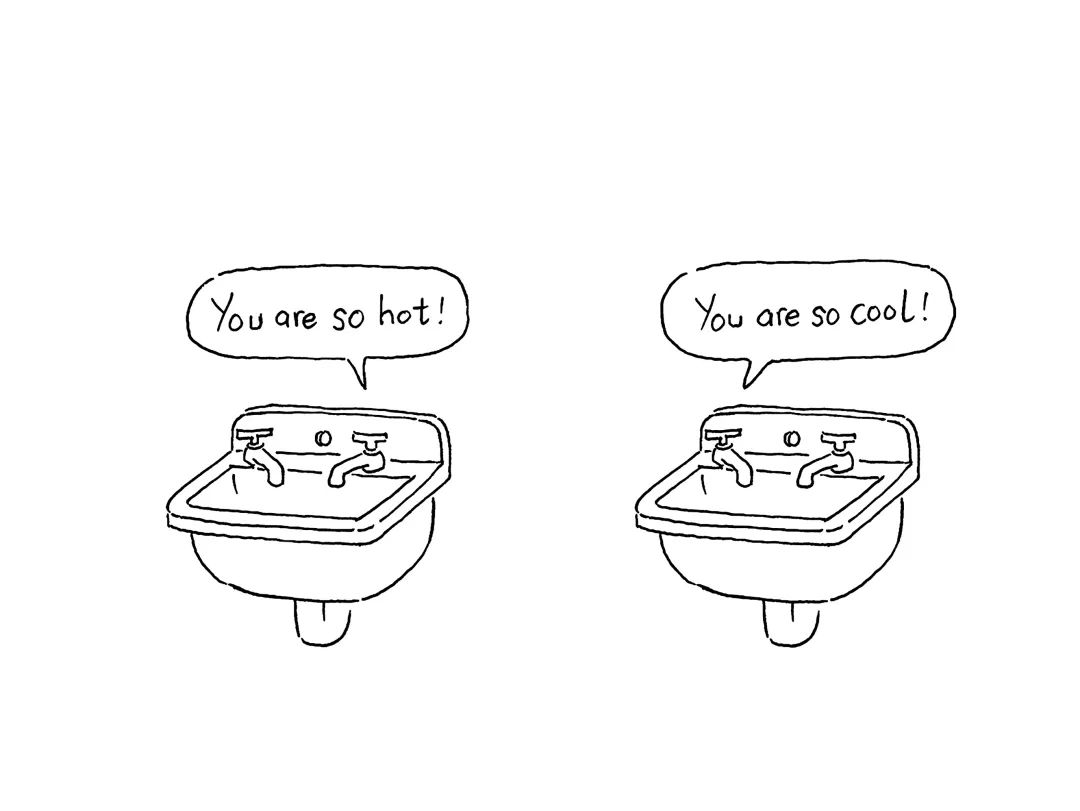
在他眼中,自己的作品从来算不上插画,更像是一份份说明书。因为文案水平有限,便用视觉创作表达自己脑袋里的概念。得益于长期受到广告事业的磨练,也从来不担心想法缺席。
这次来到上海,正好约了他在他家楼下的咖啡馆碰面。眼前的Tango身着简单的黑色T恤,一副狭长的黑框眼镜架在鼻梁上,讲起话来声音沉沉的,语速不快,却有一种洞察世事的力量。
在我们持续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对话中,他提了35次“感动”这个词。
“培养创意的唯一方法,
就是让你有危机感。”
Tango感动时,就会画画。而他每天都会感动。
“创造概念”,一直都是他创作中的关键词。每天目之所及的菜单、海报、说明书、LED屏、建筑设计,都能触动他,“可能文案是听来的一种概念,而我作为视觉工作者,就习惯这种视觉上的敏感度。”而后再将生活中感动自己的事情稍稍加工,在保留其有趣基因的基础上,使之更富生命力。运用简笔画的形式,不喜欢上色、心情好便添些阴影,只是为了快速便捷地把这份感动再现给朋友,与朋友的朋友。
Tango从来是发完微博就跑路的性格,不再费心候着评论与转发。于他看来,“这样就不会觉得每天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便也没有心理负担了是吧?”偶尔回来看留言板,只是为了捡一些“大家的智慧”来完成朋友圈的作品同步。
这些作品,老少咸宜。许多都与他的猫有关,也有不少关于当代年轻人的焦虑与孤独,每每直击痛点。记得前些天看他在深圳落地的个展,身边的女孩指着天花板角落的影子和妈妈说:“快看!那儿有只猫咪!”那是成年人需要蹲下身来才能瞧见的、跳脱出常规视角的彩蛋。
“任意门”个展之 一个人的洗手间
“我受过广告的训练,所以特别考虑消费者的感受,所以诉求对象是谁,我就一定让他们看懂。”Tango在访问中屡次提到广告从业经验对他的影响之深。
硕士研习工业设计毕业后,他苦于在彼时的专业岗位上找不到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感;同时受到外教课上播放的广告片影响,“觉得这个世界好好啊,各种类型产品都可以做(广告),把你笑翻了”,便一头栽进了广告行业,如今已过十余年。
也正是因为频繁地与客户打交道,完全按照对方的预期将方案收拾妥当,而害怕自己逐渐失去创造力。于是开始从墙面涂鸦到杂志封面涂画,再接着便在九年前,赶上了微博的顺风车。

至2019年8月,Tango已收获了143万名粉丝。
他不喜欢别人喊他“漫画家”。由于学习工业设计的关系,他的画简单得像家具装配图,概念永远走在技巧前面,源自生活,却并非一招一式雕琢生活。其次,“漫画家”的头衔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他所做的事情。
“我都是画黑白的,喜欢极简,尽量真诚,只有一点信息,所以我特别受不了客户让我填满了。”他的生活就和他的画一样,不需要很大的房子,舒服就好;在项目协作中学会妥协,也认清了自己的局限性;事情做到差不多就好,不用百分百完美。
他仍记得刚入职Y&R第一天,带他的创意总监,一位澳大利亚人,和他说:“创意、想法,就是钱。”
这几乎影响了他这十多年来的职业生涯。“所以我一直有这种想法上的危机感。如果没有想法怎么办?小孩没饭吃。就是有一种本能反应。”
对于种种创作者调整状态的习惯,Tango认为都不具备参考性,“他是凭借某种生活当中的记忆,那个时候很好创作东西,然后他永远记住那个时候的环境。只要碰到这种环境,他觉得他更适合创造,其实都不一定正确的。 ”比起营造环境,他更愿意进行一些心理建设。拿抛硬币来举例,抛100次硬币,若前80次出现正面的次数较少,那么之后就更有可能出现正面——这是日常生活中的错觉。按照概率论中的独立事件,每次抛硬币都还是个独立事件,与之前的种种都没有关系。这位本科数学出身的创作者,将如此专业理论用到业余爱好中,“不要去想以前做过什么,你以后还要做。你就想今天我画幅画,感动一下自己,找一个有趣的点就可以了。”

这与广告异曲同工。“不能考虑消费者喜欢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消费者喜欢的,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埋在里面,靠触发事件触发出来。互联网的精神就是你都不知道哪个点,它突然就爆了。所以,你要用生活中不同的点去触动他。我就是找这种让你觉得好玩的东西。”
年轻时从4A公司出来自立门户,他也逼过自己。当时团队接了个教师节公益广告,但并没有预算。身边的伙伴忙得连轴转,Tango只得自己扛,文案摄影一手包办。数次自嘲文案水平不佳的他,却凭着一句“没有老师,你就读不懂这句话”,拿奖到手软。
他一直相信潜能是被逼出来的,也坦言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自己,情愿画的少、活得长,但还是画下去。
“孤独让你敏锐,
人一定要有孤独。”
这位鬼才社会讽刺家,已经不满足于纸上画画了。他想要做产品、做装置、玩跨界、做立体空间。
他终于遇到瓶颈了。这几年,“一日一画”成了“一会儿一画”。用广告的操作方式把想法“倒过来变过去弄出方案来凑个数”的套路,好像突然间行不通了。“我还是一个产品导向的人,我喜欢做一个东西,看人家用着,而不是放在一本书里,就在那个面上。”
正在巡回的个展“任意门”,就是其中一项尝试。
入口的狭长过道尽头,留下了全场唯一一句文案:“睡不着的时候都在画画”。
除此之外,他不想对观众的解读作多余引导。展览划为七个主题房间,颇有心思地设置了玄机。比如,在“猫之屋”中,他就设置了一碗巨大的猫砂盆——当你弯下腰用手把水晶猫砂拨开时,才能发现埋在底下的惊喜。
或是另一头描绘现代人手机依赖症的空间里,把画错落有致地全印在了地上,深深浅浅的脚印诉说着曾经来过的观众看得多么用力。
边上的启示之屋布满了回形针佛像,而天花板则投上了上帝的日常,身边的人来了又去,适合自闭。
尽管在其中,人们还是不可避免出于习惯地掏出手机互相影响。但Tango表示,展览的设置是为了互动,而非出于拍照目的。他始终坚持,内容是90%,网红打卡传播只是它的附加值。
这场巡展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孤独的偏好。孤独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喝酒、养猫、寻找信仰,或是在一个人的马桶上坐着,什么也不做。
“人是需要孤独的。不然就会大片时间被别人牵着做事,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就滑手机、睡觉,然后早上起来又做些什么,被一个程序一直调用着。你没有自己的感受了。”
孤独,正是面对自己最好的时候。“我最喜欢家里停电,突然让你觉得有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做什么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是吧?不要去怪塞车、误点,都挺好。因为你本来就很被动,被人安排好了。但是有一个突然打破的情况,也是被安排的孤独。”
他很珍惜在这些碎片中游来游去的片刻,往往能迎来他创作上的灵光一闪。
“可能我只适合在城市当中创作。”
Tango出生成长在上海法租界。“但我特别不想说这件事,因为感觉好像很得瑟。”
数年之后他去法国,发现梧桐树光影的比例、马路的尺度都与自己住的地方相像。法租界于他来说,有一种天然的归属感。


©️Garfield
小时候,弄堂里生活着特别多艺术家。三楼住着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每逢周末就举行音乐会,器乐悠扬的演奏盘桓在楼道上空久久不散。隔壁是美院老师,免费教绘画。老师的太太是大提琴家,同时教授乐器,在Tango学画期间,边上有成群的女同学欢声笑语进进出出,“对小男生来说,有很多女生在拉琴,就觉得这音乐好美啊”。
从幼儿园到高中,他都没离开法租界。甚至是考大学,也就近选择了家旁边的交大。直到硕士,他心想,不能一辈子都待在这儿,连外滩都很少去过——于是收拾行囊北上。自儿时学画开始,再到后来选择与专业八杆子打不着关系的广告行业,父母从来支持他的任性。
访谈快结束时,Tango与我分享了两个关于绝版的人生经历,我颇受触动。
有一次他回到北京,晚上吃完饭朋友和他说:“我带你去看个很好的地方。”
“你就告诉我在哪儿,我哪儿都去过。”
“不要,跟我去。”
那时候还没通地铁,为了方便居民通行,入夜之后东华门和西华门便可以通行,午门也是开放的。接近凌晨时,他们来到了午门前。广场空无一人,城墙的灯全熄灭了,月光斑驳洒落牌匾上,金光闪闪。在一片黑暗的静谧下,经历了近六百年风霜的建筑暗自雄伟。那时的他突然理解了:“皇城根人的傲慢是从哪来的”。
朋友和他说:“这是我谈恋爱的地方,一谈一个准。”
“我一下子觉得,有趣的人或者有幽默感的人,其实并不需要有什么技巧,他只要能看到,能够分享,就够了。”
另一次是在巴黎。朋友带他去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区。其中坐落着一处蜿蜒曲折的桥,在桥拐弯的那个点,平时总是分道扬镳的埃菲尔铁塔与圣心大教堂,居然在两侧低矮的居民楼中,被框到了一起。“这是我谈恋爱的地方。”朋友说。
“我觉得谈恋爱是最有创造力的。遇见感动你的事物,你就赶紧带去感动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种精神就很好。一切创作就是从平常之中去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东西和人分享,把人感动了。 ”
生活在城市中于Tango而言,就像翻书一样,每一页都遇见不同的人、发现不同的细节,翻过就过了。新潮的事物快速更迭,阳光底下满是自己未曾认识的新鲜事,可能它们曾经也借由不同的媒介、不同的道具存在过。
但人类在日转星移间往往显得渺小,却总还是要去探索发现更为微小的事物,彼此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