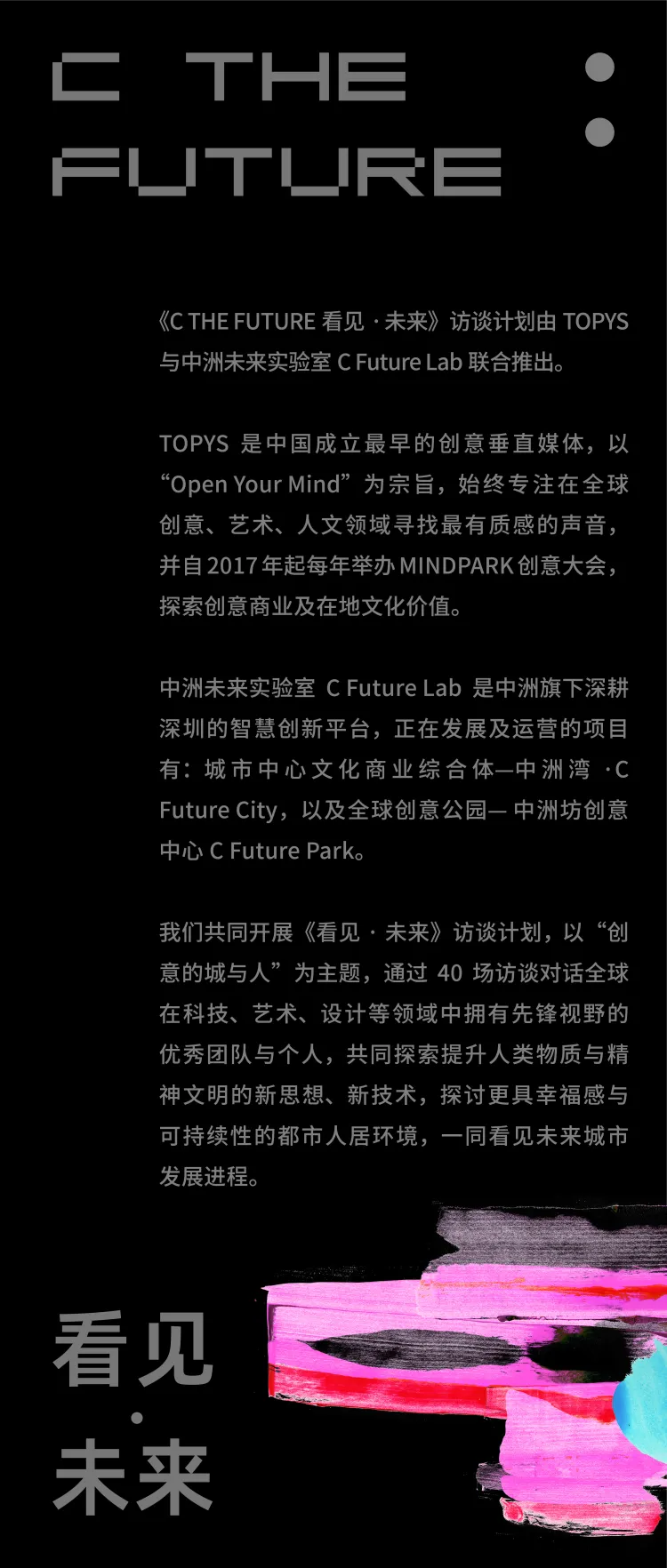置身在深圳的创意产业当中,常常会感到迷茫。自2009年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将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行业以来,作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速度更是有目共睹。但在急速前进的浪潮当中,我们也常常会想停下脚步思考:我们从哪儿来?又往何处去?
不,这次我们不再想从业内寻找答案。作为局中人的他们自然可以说出行业沉淀里的真知灼见,但这次我们更想踮起脚尖,越过信息茧房的那道墙,去看看创意界外面的观点,和那些关心深圳创意发展的非传统意义上的“创意人”聊聊,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深圳这座城和属于它的创意产业。

在深圳南山蛇口的一家咖啡店里,空气中飘散着咖啡的氤氲。四周有点吵闹,点咖啡的喊单声和谈天说笑声此起彼伏,店里还有两只猫咪,它们时不时地向路过的客人们放肆地撒娇。
这样的场合,似乎并不适合做深度采访,但当我们开始采访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被她所抛出的观点所吸引,完全忘记了外界的杂音。如果墙会说话,它一定会惊讶地感叹:两个根正苗红的中国人居然会如此聚精会神地听一个美国人讲述深圳的故事。

1995年9月,还是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文化人类学博士候选人的马立安第一次来到深圳,开始为她的博士论文做田野调查,这是她和深圳缘分的开始。
随着在深圳居住时间的加长,马立安对于城市过去与现在的发展也越来越了解。回顾深圳的过去,她慢慢地发现人们对于深圳有着各种各样的误解,“深圳不是落后的小渔村”,马立安对我们说。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组成了深圳人,不同的移民带来了文化的融合;临海的地理位置让此地盐业的发达,本地的多元文化让居住在深圳的人们开始进行跨境贸易,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尝试,探索起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也许,深圳对于经济模式的探索早于我们的想象。
时光荏苒,昔日的田地与新村在时间与政策的催化下完成了蜕变。在那样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鳞次栉比的“握手楼”(指楼与楼之间间距太近的楼房,多为本地村民自建楼房)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齐齐生长,快速构建出了一座水泥森林。

而成为经济特区之后的深圳,用一句“来了就是深圳人”吸引了大批人士前来寻求发展机会,白天涌入写字楼里工作,夜晚回到“握手楼”里沉睡。然而这一句响亮的口号之后其实暗藏了一个不可言说的“主语” —— 外地人。深圳要做创新创意创业之都,必须要吸纳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而这些人在为深圳奉献之后需要有一个身份定义,成为新一代的深圳人。
创意产业并非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是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要想读懂深圳的创意产业发展,马立安认为:我们或许该把目光从名声赫赫的大公司身上收回来,在那些散落在华强北深处的小店寻求答案。“苹果(Apple)在2018年才推出双卡双待功能的iPhone,我们的华强北在2003年就有支持双卡双待功能的山寨机了”,市场的文化和需求是激发创意变现最直接的途径,而这些不可见的文化和需求其实就藏在那些“城中村”(城中村是指留存在城市区域内的传统乡村)的握手楼中。
而这可能就是马立安为什么要开展“握手302”的原因:让艺术介入社会,为本地人诉说本地的故事。

“握手302”最初是马立安从 2013 年开始在深圳的一个名叫白石洲的“城中村”启动的一系列公共艺术创作,得名于项目诞生之处的门牌号。马立安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将艺术还给每一个对它感兴趣的普通人,为城市中难以获得公共文化资源的区域引入文化活力,发现社区的生活智慧并将它们分享给更多人,用艺术发掘城市空间的潜力。” 而在通过创意实践的过程中,马立安发现深圳创意产业的发展未必要追寻国际上既有的,如百老汇一般的发展范例,应该去找一些深圳人真正频繁接触的媒介,比如在手机上衍生的公众号与短视频。“如果深圳真的有一些艺术,真的有一些创意在出现,它应该是跟手机相关。” 马立安如是说。


“握手302”并没有给马立安带来很多经济上面的价值,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喜爱。在提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这并不常见。

马立安认为“握手302”这个项目产出了无比的价值,它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记录下了深圳的动态,生产出了属于深圳本土的价值观,相比用金钱能够衡量的经济价值,作为文化人类学者的她更关心的是“谁收割的这些价值”,即这些价值最后对谁有利?而这些价值的流动,往往是隐形的。
马立安用几个俏皮的比方来阐述她的观点:老师与学生通过共同努力取得了好成绩,校长收获他们产出的价值;春天万物生长,植物开花结果,动物通过食用它们,收获植物创造的价值;中国台湾寺庙里的义工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妇女,但作为男性的庙祝却拥有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力,庙祝并非是创造价值的人,却拥有收割价值的权力。我们的行为都会产生价值,创意生产的价值无所不在,当我们关心创意产业的发展时,我们也许在讨论的是这些价值到底流向何方?

还是要回到土地,作为创意工作者的我在采访中曾抱怨过深圳高昂的房租,“城中村”的村民们通过修建“握手楼”租赁给外来人士获取到了不菲的收入。顺着这个逻辑而言,创意的价值是不是流向了深圳原有的村民?
但马立安认为:村民们可以通过土地发财,这并没什么不对。在深圳刚刚建市之时,本地居民并没有太多接受教育的机会,“那时深圳只有三所高中,所以上过小五以上的教育就能算知识分子”,涌入的大批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说着普通话的新移民进一步缩进了本地人的生存空间,他们在故乡产生了一种“被排斥”的幻觉,只能依靠手上的生产资料(土地)来获得更好的生活。

如果支持村民们通过土地获得创意的价值,那么面对高昂的租金是否会减少深圳对于创意人才的吸引力呢?马立安说她很支持年青人的躺平态度,“辛辛苦苦每周工作六七十个小时买不起深圳一平米的房,还不如躺平写一首诗,躺平谈个恋爱呢!”在马立安看来:只有当外来者也体会到本地人被“排斥”和“剥离”的感觉,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创意的能动性,去寻找到解决方案 —— 似乎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壮烈。
过去的深圳或许执行的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为了生存不断地抢夺资源。但今时不同往日,现在主流的行为是连接,是通过资源整合来创造更多创意的价值,是一个需要“多看看自己设计的场域能怎样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时代。
创意的价值也许隐形,但并不是没有。“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收割自己创意的价值”马立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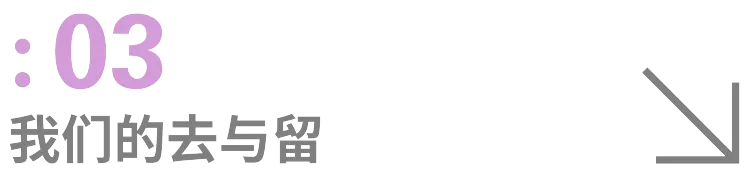
深一代有两种人,赚到钱的和回不去的。马立安笑着对我们说:“而我属于回不去的”。让马立安留在深圳的不止是她对这座城市的好奇。
马立安的先生杨阡是一名工作和生活在深圳的创意工作者。1994年,杨阡来到深圳,现为自由艺术家、深圳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和深圳市胖鸟剧团艺术总监。十余年前(2011年),杨阡的科幻剧《曼陀罗》在深圳上演,作为编剧的他将对深圳的感情融在了剧中 —— 永生一般的“无欲无求”不是深圳人所追求状态,深圳人所追求的敢于试错,敢于为错误买单,从错误中获取新知。
而这样的深圳精神,也是创意生长的天然温床。STONE STAGE的主理人蔡蔡对此深以为然。作为“深二代”的她,不断地用“试错”的经历去探寻生命中的去与留。

“深圳人做创意应该就是很野吧。”蔡蔡笑着说。
学习室内设计出身的蔡蔡,在拿到国外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因为突然的兴起跑去当摄影助理。后来又从事产品设计工作,三四份工作换下来,工龄也有两年多。正当她考虑辞职休息一段时间的关口,接到胖鸟剧团打来的电话 —— “你要不要来给我画儿童剧的舞美?”从此正式踏入戏剧圈,开始了长达六年多的自由职业者生涯。
这样的经历在深圳确属特例。蔡蔡告诉我们,设计同学们留在文化创意圈的不足1/5。“大家都去搞钱去了。” 深圳人对于金钱的执着早已名声在外,用金钱来衡量自己创作的价值。也许是对创意的热忱成为蔡蔡不断尝试的动力,在个人航线的不断调整过程中,蔡蔡用了极大的耐心向家长阐释和介绍个中缘由,“我可以跟家里讲我在做什么样的设计,(他们)慢慢会理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个性冲刺后,蔡蔡也发现深圳这座城市在本土文化发展的局限性。“深二代”依然执着地“搞钱”,外来者对于本地文化不甚了解,似乎深圳本地的创意产业并没有产生一股社会合力,经常在物质回报与精神产出之间横跳,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现实与理想是一个个“鸡生蛋、蛋生鸡”型的永恒哲学争执。但即便深圳的创意行业依旧处于一个“萌新”的状态,像蔡蔡这样的“深二代”,依旧在努力。
“当你成为一个freelancer(自由职业者)时,这个城市变得好大好大。”偌大的城市中倘若听不见回声,一种独行感将会如影随形。好在,蔡蔡身上的拼劲和光芒吸引到了同样认可美与创意的伙伴。有了志同道合的团队,蔡蔡开始思考如何以更低的门槛让艺术和创意走入生活。由此他们策划了STONE STAGE的第一期活动——“虎度门”。

虎度门,原指粤剧里演员出场的台口,在表征和象征的双重含义中缩短了人与艺术的距离。而这也就是第一期项目“虎度门”的由来。进入了STONE STAGE,就踏入了“虎度门”,一切都交给舞台,“你是戏中人了,也跟城市,然后包括这小小空间有一种(连接)。” 蔡蔡如是说。
深圳对蔡蔡而言,是生长的地方,但她却对深圳这座城市本身并没有很深的依赖。如果非要说依赖的话,蔡蔡认为除了家人朋友之外,那些积累起来,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其实是让她留在深圳的原因。因而“虎度门”的收官便选择了“剃头”这么一个生活仪式。在她曾对她的发型师说:“我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我要再怎么去找到一个让我这么信赖的人?即便所以其实剪了一个很普通的头发,我就觉得好像你来我就会安心。” 在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蔡蔡把理发师请到了STONE STAGE。天为幕,地为台,缓缓上演一出人与城的相互塑型。

蔡蔡对于深圳创意产业的现状并不满意,太多的努力流于零散。虽然“社工也很在很努力地做”,但因为力没往一处使,最终的呈现“感觉像在打乱拳” 在快节奏的深圳速度里,时间筛选掉了那些众人认为“无足轻重”的东西,人们关注的是名气与品牌,而非生活在身边的事物。但即便如此,蔡蔡“还是希望大家都多关心深圳创意产业发展。”
有感于这种微妙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依赖感和深圳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蔡蔡准备做一些跟人文有关的项目,将视角对准到这些外来者身上。“我所要呈现的不是要讲说他们很可怜,我觉得他们也是很精彩的在活着,我想讲讲他们怎么精彩的活着。至于大众可能通过我的包装或者怎么样,会觉得原来还有这么一群人在深圳也在很努力的生活,我想了解一下大家才会引起共情。”
生在深圳,长在深圳,在深圳创意产业工作的蔡蔡,身上有着深圳创意工作者们最根本的特质——“我经常拼了,我就觉得身边的小伙伴都很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