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个把小说实实在在当成一门艺术来搞,却偏偏与诺奖擦肩最多次的小说家离开了,意外却又无甚意外地。
他的名字和死讯在一个傍晚传来,迅速在云端的世界上空汇聚起半透明的阴云,笼罩着曾经被他的文字挑逗、刺痛、恐吓、惊醒或感动的读者,重新唤起一连串堪称是米兰·昆德拉式幽默又冒犯的反应(他本人可能会喜欢):
我也曾经是走到哪里都背一本米兰·昆德拉的人啊;
这下彻底与诺奖擦肩了……
米兰·昆德拉,竟然还活着?
是啊,那个曾经严肃地反刻奇,清醒地自大又不吝尖酸地自嘲,深刻又轻盈地思索存在之重的昆德拉已经94岁了,对一个这样年岁的人来说,死亡只是或早或晚会降临的夜色,连接着黑甜的睡眠。
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他想说的,都已经说尽了,留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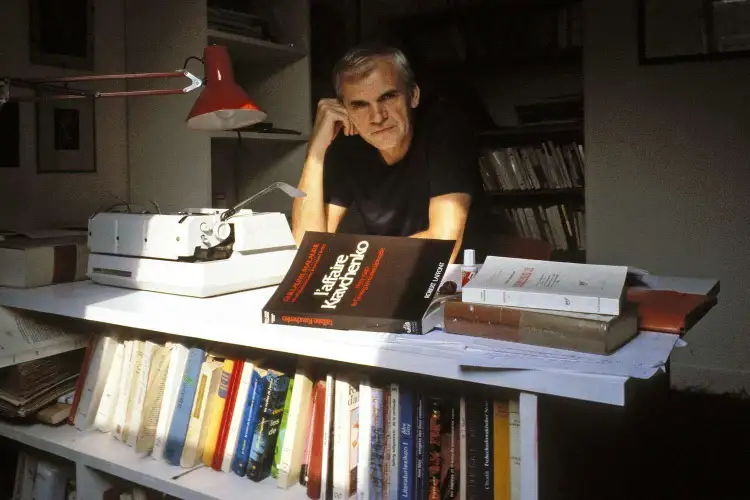
他又一次对自己说,特蕾莎是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河水汹涌,怎么就能把这个放着孩子的篮子往水里放,任它漂呢!……托马斯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比喻是一种危险的东西。人是不能和比喻闹着玩的。一个简单比喻,便可从中产生爱情。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他还说他就没有自己的家,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表达,那就是他的家正在他的脚步中,在他每一步的旅程中,在他的旅途中。说他的家就在未知的地平线开启之际。他说只有不断地从一个梦转到另一个梦,从一片风景转到另一片风景他才能够活下来,如果他在同一个环境中待很长时间他一定会死去。
——《生活在别处》
是的,我忽然看得很清楚了: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双重误信的幻觉,一方面以为记忆是恒久不褪的(记忆中的人、物、行动、人民都不变);另一方面又以为补偏救弊是可能的(补救行为、谬误、过失、罪恶。其实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一样大谬不然。事实恰好相反:一切都终将被遗忘,同时又无论什么事物都不可能得到挽回。
——米兰昆德拉 《玩笑》
性爱,这个灾祸的萌芽,靠着收集者,成为了一件跟吃早餐或者晚餐、跟集邮、跟打乒乓、跟购物一样的事。收集者使性爱进入了日常生活的平庸圈子。他把它变成舞台的幕侧或者后台,而真正的戏剧将永远不在那里上演。
——《好笑的爱》
“你从来不善于生活。你总是在想,你的义务,就像人们说的,是生活于其中。在现实的中心。但是,对你来说,现实又是什么呢?政治。而政治,是生活中最不基本的和最不珍贵的东西。政治,是漂浮在河面上肮脏的浮沫,而实际上,生活之河则涌动于深深的洪流中。”
——《告别圆舞曲》
当事物突然失却了它们预定的意义、脱离了既定秩序中应有的位置的时候(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占星术),就会引起我们发笑。最初,笑属于魔鬼的领域。它有些恶意的成分(事物突然显得与它们平时被认为的样子有所不同),也有一些善意解脱的成分(事物显得比原来的样子更为轻松,让我们更自由地生活,不再以它们的庄严肃穆来压迫我们)。
——《笑忘录》

为了医治我们自身的可悲,比较常见的药方是爱。因为绝对被爱的人是不可悲的。所有那些缺陷都被爱的神奇目光补救了,在爱的目光下,脑袋挺立在水面上的笨拙的泳姿,可以变得迷人可爱。
绝对的爱实际上是追求绝对同一的愿望:我们爱着的女人应该和我们游得一样慢,她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会幸福地回忆起来的过去。可是,一旦绝对同一的幻想破灭(姑娘幸福地想起她的过去,或者她快速游起来),爱就成了不断产生我们称之为力脱思特的那种不尽烦恼的源泉。
——《笑忘录》
这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可是,被我们祖先的上帝遗弃是一回事,被宇宙电子计算机神圣的发明者抛弃又是另一回事。在他的位子上还有一个即使他不在仍在运行的、其他人无法改变的程序在起作用。编制电子计算机的程序并不意味着未来的细节都得到详细规划,也并不意味一切都被写进“上天”这个程序里。譬如说,程序并未规定一八一五年要发生滑铁卢战役,也没有注定法国人要遭败绩,只是规定了人类的进攻本性。有人就有战争,技术进步将使战争日益残酷。从造物主的观点看,所有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是总程序中的一些简单的变化和转换游戏;而总程序与未来的预测毫无关系,只不过规定了可能性的范围。在这些范围以内,它完全让偶然性来起作用。
——《不朽·脸》
她突然为这种仇恨感到害怕。她想:世界已经走到一个极限,如果再跨出一步,一切都可能变为疯狂。人们都将手执一株勿忘我走在街上。他们互相用目光射杀对方。只要很少一点东西就够了,一滴水就能使坛子里的水溢出来,那么街上再增加一辆汽车,一个人或者一个分贝呢?有一个不能逾越的量的界限。可是这个界限,没有人注意它,也许甚至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不朽·脸》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这里,在这座公园里,在我们面前,您瞧,我的朋友,它就绝对明显、绝对天真、绝对美丽地存在着。
——《庆祝无意义》
人们习惯于把出神的定义与重大的神秘时刻联系在一起。但是,生活中有的是日常的、平凡的、庸俗的出神:愤怒中的出神,高速行车中的出神,震耳欲聋的噪音中的出神,足球场上的出神。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努力,努力使自己不至于迷失方向,努力使自己在自我中,在原位中永远坚定地存在。只消从自我中脱离出来一小会儿时间,人们就触到死亡的范畴。
——《被背叛的遗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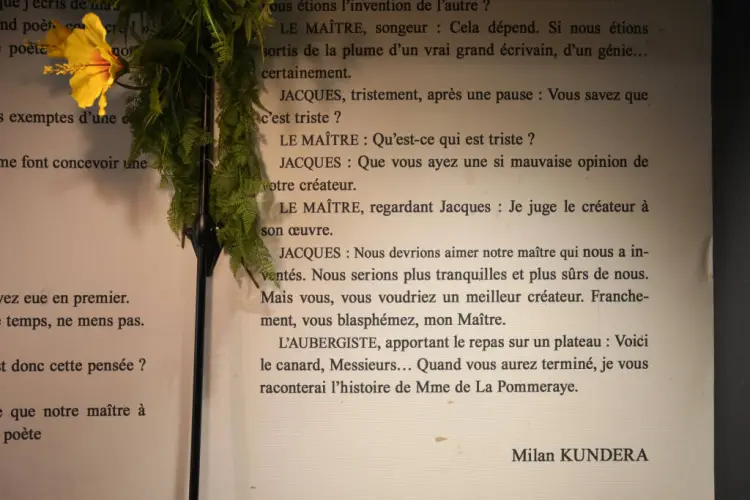
可惜呀,奇迹只持续短暂的时间。腾飞的,有一天终会落地。我深感焦虑,想象有一天,艺术将不再去寻找从未说过的东西,而会乖乖地为集体生活服务。集体生活将要求它使重复显得美丽,帮助个体祥和地、快乐地混入生命的一致性中。
因为艺术的历史是会灭亡的。艺术的叽叽喳喳是永恒的。
——《帷幕·永恒》
美学概念只是在我看到了它们的存在根源时,在我把它们当作存在概念来理解时,才开始让我感兴趣。因为,人们不管是简单的还是优雅的、聪明的还是愚蠢的,都在他们的生活中不断与美、丑、崇高、喜剧性、悲剧性、抒情性、戏剧性、行动、曲折、升华等概念相撞击,或者用一些没有那么哲学化的词,与不懂幽默的人、媚俗或平庸相撞击。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引向存在的不同方面的佳径,这些方面通过其他任何手段都是不可及的。
——《帷幕·美学与存在》
将人类重大的冲突从善与恶斗争的天真解释中解脱出来,并在悲剧的照明下去理解冲突,乃是人类智性一种巨大的能力。它使得人类真理致命的相对性显示出来。它使人感到一种为敌人也讨回公正的需要。
——《帷幕·假如悲剧性已将我们抛弃》
懂得排除痛苦的人才是幸福的人;由于享乐带来的不幸往往多于幸福,伊壁鸠鲁只嘱咐世人享受节制平凡的乐趣。伊壁鸠鲁的明智却有一种忧郁的深层含意:人被抛入悲惨世界,看到唯一明白可靠的价值是乐趣,虽则它多么微不足道,还总是他本人能够体验到的乐趣,如喝一口清水,看一眼天空(面对仁慈上帝的窗户),抚摩一下。
——《慢》
我无意主张艺术作品乃圣洁不可冒犯。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也重写了许多别人的创作,但是他并没有去改编什么东西。他所做的,是把别人的创作拿来当作自己变奏的主旋律,而在其间,他仍是独立自主的作者……您若问我为何要就这些事长篇大论?那是因为我想和雅克的主人一起大喊:“人家写好的东西,胆敢把它重写的人去死吧!最好把这些人通通都阉掉,顺便把他们的耳朵也割下来!”
——《雅克和他的主人》

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就这样掉进了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用一个漂亮的、几乎神奇的叫法所称的“对存在的遗忘”那样一种状态中。
人原先被笛卡儿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结果却成了一些超越他、赛过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
——《小说的艺术》
在小说家与不会笑、没有幽默感的人之间是不可能有和平的。那些人从未听到过上帝的笑声,坚信真理是清晰的,认为所有人都必须想同样的事情,而且他们本人完全就是他们所想的那样。但是,正是在失去对真理的确信以及与他人的一致的情况下,人才成为个体。小说是个体的想象天堂。在这一领地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掌握真理,既非安娜,也非卡列宁,但所有人都有被理解的权利,不管是安娜,还是卡列宁。
——《小说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