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建筑界,马岩松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和代名词。
作为首个拿下海外地标项目的中国建筑师,他似乎永远在做人们意料之外的事。在他笔下,那些行云流水的曲线时而流露出赛博朋克的未来气质,时而又如一阵远古的风将人带回自然深处。但无论面向哪种时空,他的设计总是充满一股反叛的劲儿。
在采访前,我本以为马岩松的性格会和他的建筑一样,特立独行甚至有些锋利。但当语音接通,电话线另一端却传达出一种温和且憨厚的气质。他笑着说有这种反差很正常,建筑师本就是幕后工作,先看到作品再见到人,难免会有先入为主的印象。“有的人作品看着很刺激,但本人却比较温和。”

接触下来,很难不认为马工这句话是在形容他自己。在被提起太多次的天才标签背后,是围绕他的建筑久久不散的讨论。喜欢的人认为他独特前卫,不喜欢的则直言他的建筑奇怪且格格不入。但无论你喜不喜欢他的设计,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当今在国际建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建筑师之一。
近日,马岩松在深圳举办了个展“马岩松:流动的大地”。这是MAD建筑事务所自创立以来规模最大、最翔实的一次展览。借此机会,我们和马岩松聊了聊他最新的作品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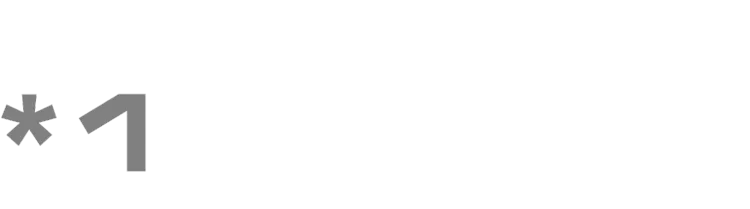
是建筑师,也是艺术家
TOPYS:在流动的大地展览中,你把一只海鸟雕塑放在展馆中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马岩松:这个海鸥雕塑是我以前的作品。之前在荷兰鹿特丹做FENIX移民美术馆的时候,我设计过一个海鸥雕塑。移民的人是离开了家乡去一个未知的地方,会面临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但当时我去荷兰的时候看到好多海鸥,它们看起来非常自由自在,想吃东西就吃东西,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去,不像人会有身份焦虑。后来在米兰设计周,我做了一个更大的海鸥雕塑。那时候正好是疫情,我就叫它Freedom,它的姿态定格在从老建筑飞出去的那个瞬间,我想通过它传递一种自由的感觉。
所以它象征着个体的表达和自由。建筑虽然不能直接产生影响,但还是可以提供这种感受。人们住在一个管制型的建筑或城市空间里,跟住在一个能启发人、让大家有意愿去自由发声和讨论的空间里还是有区别的。

TOPYS:今年你在深圳的新项目“深圳北站超核绿芯”前几个月已经开工。这个项目很有科幻感,让我联想到你之前设计的“超级明星:移动中国城”。为什么偏爱运用科幻元素?
马岩松:其实科幻也是一种人文,有些建筑看起来充满未来感,但都跟具体的文化背景有关系。超级明星纯粹是一个概念作品,当时处于北京奥运前夕,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要么是功夫熊猫,要么就是惊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但我觉得这建立不起一个真实的中国。当时我们正好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就觉得应该作为中国建筑师去表达一些东西,所以设计了超级明星。它是一个能源自给的、可以降落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也叫中国城。别人看到以后,就去讨论为什么中国城会以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样貌出现。所以它看起来好像很科幻,但其实是针对当时的文化现象做出的表达。

深圳是很新、很现代化的一个城市,但这种现代化是有局限性的,还是照着一种模式去发展。我觉得需要一些探索性或试验性的未来。还有深圳湾文化广场也是这样,那个项目看起来没那么有科技感,但也是想跟现实拉开一点时空距离。
我确实对未来感兴趣,但我相信未来不只是科技怎么发展的问题,肯定还跟人的文化状态还有他的过去、他从哪里来有很大关系。这些项目就是从当下的时空中抽离,让人思考这些事情为什么是这样,所以看起来有种“不合时宜”的科幻感。

TOPYS:你为今年阿那亚戏剧节打造的候鸟沙城体量相对较小,和前面聊的深圳湾文化广场那种宏大建筑看起来很不同,你做这个项目的灵感是什么样的?
马岩松:候鸟沙城和城市里的建筑不太一样,它不符合我们对建筑应该坚固、永久甚至伟大的期待。在这个项目里面,建筑只是提供一种空间氛围,人的活动更重要一些,所以我只做了墙,没有做屋顶。你只有进去感受空间布局,参与里边的活动,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空间里完整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像一个微型城市,因为我觉得城市最终还是关于人怎么生活、怎么想象、怎么吃喝拉撒、怎么思考的。建筑和布局只是一个舞台或者载体,所以在这个项目里关于设计的东西会有意地弱一点。
而且它有存在时限,只存在300小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电子时钟在倒计时。当这300小时结束的时候,这一切就都结束了。这跟城市文明对永恒、效率这些关于时间的认知很不一样,它其实是在对抗那种价值,它传递的是一种短暂的、璀璨的,又在环境里随遇而安的感觉。

TOPYS:你这两年做了蛮多艺术装置项目,对于你来说,艺术家和建筑师这两个身份有什么不同?
马岩松:我觉得挺一样的,但建筑更复杂。艺术比较个人,就算我不喜欢它,我都允许它存在。但建筑必须要达到共识,尤其是城市里的公共建筑,大家都觉得它是自己的,所以都要发表意见。而且建筑花的钱多、建造时间长,还有各种技术限制。
但是它们也有共同点,都是关于个人的感受和思考的。可能大家以前觉得建筑和艺术应该分开,建筑就是功能性的,不用上升到情感和思考,觉得它们是两个事儿。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事儿,建筑不能没有美感。不管建筑师还是艺术家,都会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并且二者都是幕后工作。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建筑的设计师是谁,而是先看到他的作品、进入他设计的空间里。我喜欢这种在幕后观察别人跟你的作品发生互动的感觉,这是我找到的一个跟世界对话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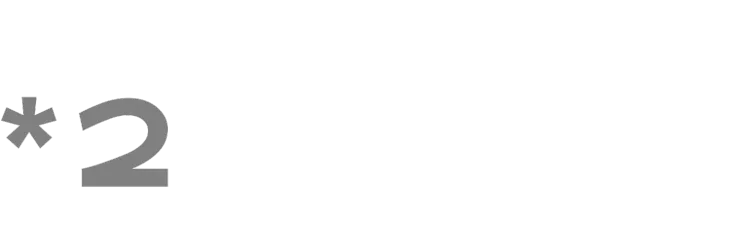
好的公共空间,能让人产生新的思考
TOPYS:什么是好的公共空间?中国现在缺少什么样的公共空间?
马岩松:我觉得公共空间的好坏,就在于它能让人产生多少思考。如果建筑空间只是功能很好、很舒服,就会让人退化,因为舒服了就不会思考。这不是好的空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空间就是完全开放、欢迎所有人来,但我觉得这不应该是绝对的标准。因为以前是太缺少公共空间了,大家想做什么都没地方去,有地方就已经很好了。但如果大家都挤在一个地方干一样的事,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意义。所以一个空间如果有艺术性,甚至有点奇怪、有点超现实、让人思考让人好奇,这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公共空间。
中国古典意境里常常会有一个亭子,里面站着一个人,我们观众看到这个图景就能立即进入那个境界。但是那个亭子里真的不能挤下好几百人,就得是那一个人。可是这个亭子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公共空间,只是他不以容纳很多人为目标,现在就挺缺少这类建筑或装置的。

TOPYS:建筑师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参与到公共事件的讨论当中?
马岩松:建筑师改变或者介入社会的方式,就是在他做设计的时候,出发点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批判上。比如他觉得未来的社会或者城市生活应该是什么样,他把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通过具体的工作表达出来。
我之前在北京做过公租房项目。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做大地标、一个城市只有一个的那种项目,但其实公租房恰恰是受限制最多、非常困难的项目。我们做了很多调研和研究,建成以后也做了好多研讨,有很多行业内的领导、大学学校内部,还有业内媒体都在讨论关于住宅和社会保障的事情。这个话题逐渐变成一个社会性的议题了,谁都可以参与进来。这就是从一个具体的建筑引发出来社会讨论。对我自己来说,看到年轻建筑师和学生的想法和思考也挺重要。

TOPYS:你做过很多地标建筑,你觉得地标建筑在整座城市中的角色,除了奠定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以外,还有别的含义或者价值吗?
马岩松:我觉得可以先聊一下地标的定义。地标应该是超越视觉的,它是一个人对这座城市印象最深刻的点。所以这种记忆肯定是多元的。如果是老建筑像故宫,它的历史文化已经摆在那里了。但如果是新建筑,我觉得它应该给城市带来一些新的理念,比如国家大剧院就是从传统跳脱出来的那种建筑。它四周都是花园,你要先经过湖水、树林,再从地下慢慢进到建筑内部。最后在一个穹顶之下,和其他艺术爱好者聚集在一起,有一种独特的场所感。
当时在定国家大剧院方案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说这个建筑跟周边环境格格不入。但我觉得如果没有定下这个方案,而是定了一个跟环境协调的方案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国际建筑竞赛,肯定不能太保守,要在兼顾市民性的同时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这种地标就是正面的。哪怕现在还有人对它的视觉效果有异议,我觉得都不重要了。它已经在文化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或者说我们跟城市的关系这些层面上实现了突破。这就是我对地标的理解,不能只从视觉上是否突兀、怪异去判断。地标肯定要做很多方面的革新,它在城市文化上一定是一个很进步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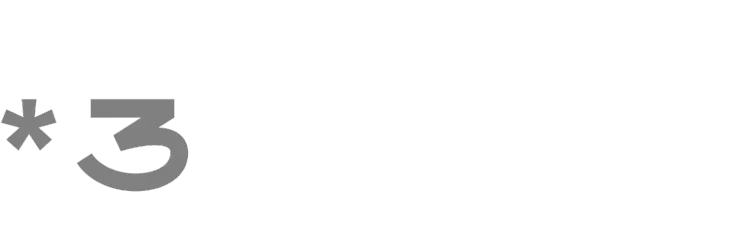
不被接受是一件很厉害的事儿
TOPYS:现在你每天会工作几个小时?
马岩松:基本一直都在工作,没有跟工作彻底分开的时间,我估计好多建筑师都没有。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沟通交流,比如像开会、汇报、媒体采访。然后出差在路上的时间也特别多,因为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去现场、见业主,熟悉当地的文化、住户。在盖的过程中也要不停地去现场,每个项目都得经历各种“打架”。我感叹过,建筑师到老了都是重复这个流程。或许你的思想会更成熟,但是你不可能不去现场。所以经常满世界跑,工作和生活就是混在一起的。这样也有好处,就是出去见到新的人、经历不同的文化,这其实也是工作需要,因为建筑最终是关于不同人的生活的。

TOPYS:你刚毕业的那段时间,在两年间参加了一百多场竞赛,才有了梦露大厦中标。在梦露大厦之前,那段高强度参加竞赛的时间是怎么坚持下去的?
马岩松:我们那时候没有绝望,就是觉得这个过程很牛。因为觉得环境很傻,所以不被接受是一件很厉害的事儿(笑)。就像那些喜欢摇滚的人,他们认为主流是一个体系,而我肯定跟他不一样。所以要是他们都接受我了,那我是不是有点问题?其实那时候好多建筑师都是挺朋克的、甚至英雄式的人物,像我的老师扎哈,她年轻的时候也没被接受,建不成房子。
当时年轻人很崇拜这样先锋的人。我刚从学校出来,也觉得这种先锋的、有批判性的东西很帅,所以当时做很多作品都不是为了中标,就是以批判或者表达自我为目的的。因为我的观点跟你们不一样,你们都想那样,但我觉得那样不好,我就要这样。以这个为出发点的话,就不会觉得这个阶段漫长了。

TOPYS:为什么你的反叛能带来如此强的创造力?
马岩松:就像我刚说的,因为我已经做好持续性不被接受的准备,所以如果有少部分人接受的话,就会给我更大的力量。我后来回想起历史中那些朋克的、理想主义的设计师、建筑师或文化人,其实都有一个团体在互相鼓励和支持,还是需要有这样的环境。
然后就是目标感吧。如果目标在眼前的话,就很容易受挫折。因为你就是想赢这个比赛,输了就会受不了。但我那时候就是希望能为自己发声,只要跟别人不一样、有独立的想法就够了。甚至做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的时候,我就想我怎么赢呢?因为当时好多有名的建筑师都来参加,从各种可能性来讲他们都不会选我。所以我就想当我输了以后,这个作品能比赢的作品有更多讨论空间、让人觉得有启发,那就够了。当然后来赢了我也很高兴。但重要的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和对这个目标的表达。得了奖是好事,被批评了也不是坏事,这都是过程,但都不是目的。

*以上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不得自私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