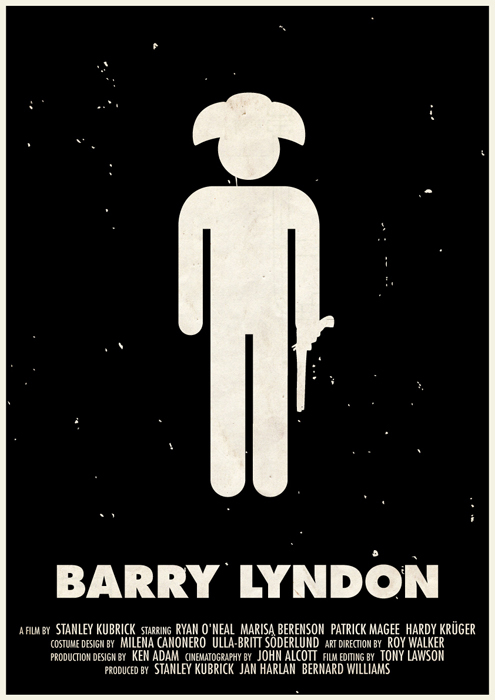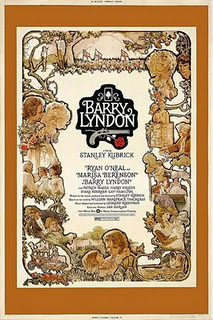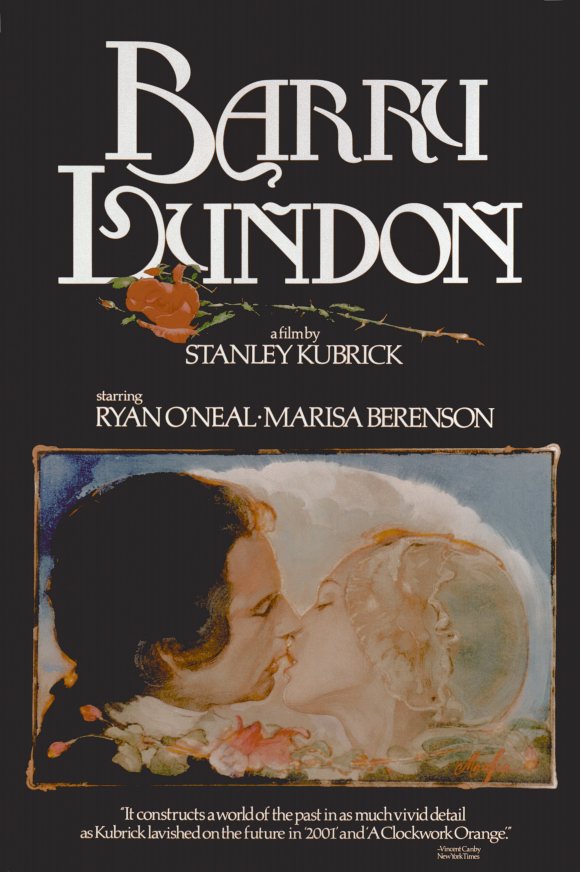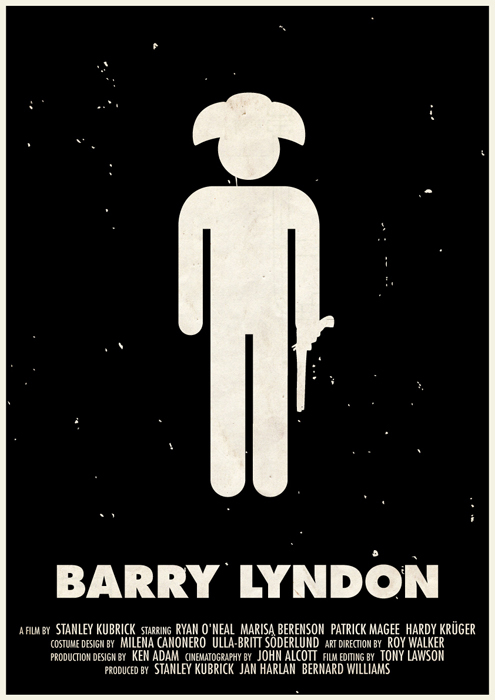
Q:米歇尔西蒙
A:库布里克
Q:你几乎没为《巴里林登》做过任何访谈。仅仅是因为这部电影呢?还是本就不愿谈及自己作品?
A:我可以找借口说这片子公映前几周才制作完毕,根本没什么时间接受采访。但坦诚布公地说,很可能是因为我本不喜欢做采访。总会有被误引的麻烦;或者更糟的是,被逐字引用,然后被迫在纸媒上看到你说过的话;然后还有那些套路——“你和演员X,Y或Z相处如何啊?”——“是谁想出了好主意,A,B还是C?”也许纳博科夫应对采访的做法最合适。他只同意写下答案寄给采访者,让对方再写下问题。
Q:是否觉得《巴里林登》是部更私密的电影,更难谈论它?
A:并非真正如此。我总觉得很难谈论任何一部我的电影。通常我的做法是聊些与故事关联的背景信息,或是一些也许相关的有趣事例。这么做可以让我躲过“这代表什么含义?你为什么这么做?”此类的问题。比如说,谈到《奇爱博士》,我可以聊各种会偶然或无意间导致战争爆发的怪点子。《2001漫游太空》可以去假想超智能电脑,宇宙中的生命和一整套科幻创意。《发条橙子》涉及到法律与秩序,暴力犯罪,当权与自由的对立等等。《巴里林登》没有这些话题性的东西,这么说来确实有点较难述及。
Q:你之前三部电影都设定在未来背景下,怎么会想到拍古装片的?
A:老实讲,我没法说清楚是什么驱使我拍任一部电影。最多只能说是我爱上了这些故事。再说下去就变得有点像解释为什么会爱上自己的妻子:她聪明,有褐色眼睛,身材不错。这么说有实质意义吗?鉴于我正处于决定下一部拍什么的阶段,我认识到找故事这事有多难掌控,对运气和灵机一动有多依赖。你可以说出很多电影故事应具备的“基本”要素:有力的剧情,有趣的人物,有空间供电影语言发展,有机会让演员展示情感,真实而聪明地呈现影片的戏剧主题。可当然,那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会选那个,也不会带你找到一个故事。只能说,你大概不会去选一个没有多数上述特征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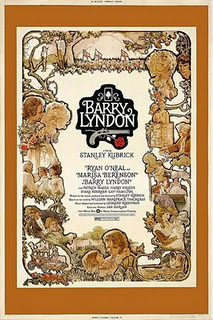
Q:既然你对故事素材选择有全盘自由度,那怎么会选上一部萨克雷的小说,一部几乎被遗忘且十九世纪后鲜有重印的小说?
A:我有一套萨克雷全集,在我家书柜上搁很多年了,《巴里林登》之前我已经读过几部他的小说。我一度动过把《名利场》拍成电影的念头,但到最后,我认定这故事没法成功压缩到一部电影长片的较短时间里。顺提一句,这个时长问题,现在已经被电视迷你剧完美解决了,它长度在10-12小时,分几晚播放,开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戏剧载体。话说回来,我一读到《巴里林登》就激动不已。我喜欢这故事和角色,小说看起来也能被成功搬上银幕而不至于被玷污。这样也提供机会来做到一桩电影盖过任何其他艺术形式的东西:呈现历史题材。描述这东西对小说来讲有难度,但电影可以轻而易举做到,至少就满足观众层面而言。科幻与幻想题材同样如此,它们所提供的视觉挑战与可能性很难在当代故事中找到。
Q:你怎么会想到采用第三人称旁白方式,而不是沿用小说里的第一人称叙事?
A:我相信萨克雷是故意用雷德蒙巴里来半真不假地讲自己的故事,因为这样更有趣。与其使用全知视角,萨克雷选择了不完美的观察者,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不诚实的观察者,这样就给了读者一点挑战,来自行判断雷德蒙巴里描述的一生究竟有多少真相在。这种手法在小说中非常奏效,但在电影里,你得面临时间限制这个客观现实,所以萨克雷独特的第一人称叙事没法在银幕上重演。也许把巴里口述真相与银幕呈现事实并置会很有喜剧效果,但我不觉得《巴里林登》应该拍成喜剧。
Q:你从来没想过不用旁白吗?
A:片子有太多故事要讲。用旁白可以免去用很多解释性对白场景作铺垫的尴尬,那样会很乏味又多半不可信:“该死的狂风毁了我们的幸运船!” 旁白,作为另一种选择,既可取又经济,可以完美传达那些无需戏剧沉淀的故事信息,又不显得臃肿。
Q:但你用旁白还有别种功效——抑制场景中的感情元素,以及预告下面的故事。比如,就在遇上快乐的德国女孩后——一段很动人的场景——旁白把她比作了一座经常被攻占的城镇。
A:你所说的这场戏,旁白的作用是观众所见表演的反讽注脚。这只是整个故事中很小的一段戏,所以必须以经济的方式呈现。巴里对女孩很温柔很罗曼蒂克,但他真正想的是骗她上床。女孩很寂寞,巴里帅气又殷勤。用心想的话,女孩的丈夫从军去了,巴里不太可能是她带回家的唯一大兵。你可以让巴里用表演来提醒观众,暗示他并无诚意,纯是投机取巧,但这么拍就不真实了。大家想骗人时总会扮得很真,不对吗?
这部电影的旁白还有另一种功效,但这个就和小说基本一致了。这个故事有很多变化与转折,萨克雷让巴里在多数重要剧情发展出现前就给出暗示,这样一来,转折就不显得那么刻意了。
Q:他去见巴里巴瑞骑士前,旁白预告了我们将要见到的情感转折,这么做也许削弱了这场戏的感染力。
A:《巴里林登》的故事不仰仗惊奇。重要的不是将要发生什么,而是如何发生。我想萨克雷这么做是舍弃惊奇的益处,来换取强有力的宿命感,也更好融入了否则会显得狗血(melodramatic)或刻意的剧情。你提到这场巴里去见骑士的戏,是旁白奠立了让两人迅速成为好友的基础。通过描述巴里由思乡而生的寂寞,作为放逐人士的孤立感,和异国遇老乡的欣喜,旁白为这场戏作了铺垫,巴里与骑士一应即合也就水到渠成。电影中还有一处让我觉得这手法尤其奏效,观众看着巴里和幼子布赖恩快乐嬉闹,旁白却道出后者即将死去。在这里,我觉得旁白营造的戏剧效果就如同,打个比方说,大家看泰坦尼克号无忧无虑作准备并启航,却都知道它注定沉没。要是观众不知道这艘船将要撞上冰山,这些前戏就会显得极为无聊。提前道出将要发生的灾难,这么做舍弃了惊奇但营造出悬疑。

Q:电影中很少有自我反省。开始阶段,巴里会公开道出他的情感,但后来就很少了。
A:故事一开始,巴里身边围绕着更多人,可供他吐露情感。等到故事发展开来,尤其在结婚后,他变得越来越孤立。到最后再没人爱他,他也没人可吐露心声,也许还有他的幼子,但年纪太小还帮不上忙。同时我也不觉得缺少自省对故事有任何损失。巴里的情感在他应对人生愈来愈多的困境时清晰可见,我觉得故事中的其他角色同样如此。无论何时,人们谈论自己的戏经常都很无聊。

Q:和那些忙于分析角色心理的电影相反,你喜欢维持角色身上的神秘感。举个例子,朗特牧师就是个很隐晦的人物。很难完全把握他的行事动机。
A:但你也对朗特牧师了解不少,必要的都有了。他不喜欢巴里。他以自己拘谨的、压抑的、低调的方式暗恋着林登夫人。电影快结束时那场马车戏里,他那一抹胜利的浅笑,告诉了观众需要知道的一切,他是怎么看巴里的不幸啊,他对事情的结局感觉如何。肯定没时间在电影里发展小角色的动机。

Q:林登夫人甚至更晦涩。
A:萨克雷在小说里写她也不多。我觉得挺怪的。他没给你多少空间。实际上,小说中她的对白戏非常少。也许他想给她一种神秘感。但至少电影给了足够的信息来了解她。
Q:你的改编作了些重要变动,比如发明了最后的决斗,以及结尾本身。
A:是的,的确如此,但我觉得这些保留了小说的精髓,故事的结局和小说基本一致,只是时间缩短了,对此我很满意。小说中,巴里是被林登夫人用年金打发走的。布林顿公爵从美洲回来了,尽管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他找到巴里给了他一顿好打。巴里在母亲的照料下,最后死在监狱里,死的时候是个酒鬼。这些,和小说里其他配套的故事改到电影里就太长了。电影中,布林顿复仇成功,巴里被彻底击败,大家可以想象,他最终的结局不会和小说有多少区别。
Q:两个同性恋湖中洗澡那段戏书里面也没有。
A:这里的问题是如何让巴里逃出英军。书中的情节也很长很复杂。
设计两个同性恋军官就是给巴里一个简单的逃离方法。还是那句话,方式不同,但最终结果与小说一致。巴里偷了英国军官的文件和制服,得以逃向自由。既然这场戏纯是解释功用,喜剧化处理能帮助观众集中注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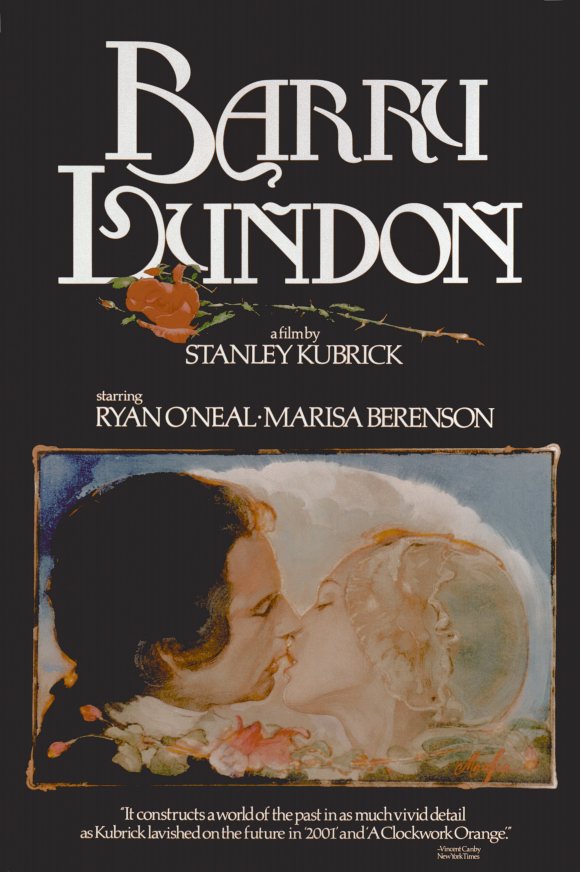
Q:是否刻意安排了片中一些反复出现的元素:如军中的鞭刑,家里的鞭打,决斗等等,还有那与《发条橙》相似的叙事结构?是不是这种几何对称很吸引你?
A:对称叙事更多出于讲故事需要,而非刻意设计的产物。在制作电影的艺术流程中,如何发现和执行计划一样重要。编写一部剧本,首要责任是钻研原作者的意旨,确保自己明了他的所写,和为何而写。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废话,但就这点常有人做不到。编剧容易很快落入“创造”的滥斛。下一步是确保故事能经得起筛选、压缩的考验,控制到最好两小时,最长不过三小时的限度内。这一阶段通常会决定巨著改编的命运,它们非常仰仗于宏大的画卷来呈现。
Q:《发条橙》的上半部,观众站在亚历克斯对立面。到了下半部,我们倒向了他那边。在这部电影里,对巴里既怜爱又厌恶的情绪贯穿始终。
A:萨克雷把它称为“一部没有英雄的小说”。巴里天真无知。他一直被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野心所驱使。两种特质合到一起成为灾难,最终导致了他和身边人的不快乐与悲剧。观众对巴里的感情是混杂的,但他很迷人也有勇气,尽管有虚荣、不体贴和软弱的一面,大家还是很难不去喜欢他。这是个很真实的角色,既不是传统意义的英雄,也不是传统意义的反角。
Q:观众到最后的感觉是一种彻底的浪费。
A:也许更多是种悲剧感,因为这个故事有曲折变化的情节,又不算狗血(melodrama)。情节剧(melodrama)用了全世界的问题,和降临到角色身上的困苦与灾难,来向大家展示这终究还是个公平仁慈的世界。
Q:最后那句话说所有角色现已等同,这可以被视作是虚无主义或宗教的宣言。从你的电影看,人们觉得你是个试图相信的虚无主义者。
A:做下功课就知道那只是从小说摘来的反讽后记。它的含义我觉得很清晰,而且,至少对我而言,这和虚无主义或宗教都扯不上边。

Q:人们觉得你的电影世界永远处在战斗中。《2001漫游太空》的猿人在战斗,《光荣之路》和《奇爱博士》也有战斗。《巴里林登》的上半部有场战争,到了下半部,观众发现家也成了战场。
A:戏剧就是冲突,暴力冲突不只在我的电影里有。由暴力冲突驱动的电影也不罕见。说到《巴里林登》,通过斗争成功获取财富和社会地位后,巴里很不适合这个新角色,一踏进去他的人生就变糟起来。这些角色和之间的关系注定了随之而来的暴力冲突。早期斗争带巴里迈向新人生,给他带来冒险和幸福,但后期斗争带来的只有痛苦和悲剧结局。


Q:有许多方面,这部电影都让我们联想起默片。尤其是赌桌前引诱林登夫人那段。
A:说得没错。我觉得默片成功之处多过有声片。巴里和林登夫人坐在赌桌前,眼神都在对方身上流连。二人一言未发。林登夫人起身去阳台透透空气。巴里跟着出来。他们热切地互相凝视最后接吻。还是没说过一句话。这很浪漫,但同时,我觉得也暗示出两人互相间的吸引是空洞的,热情消褪起来也会一样快。这为接下来二人关系所有发展奠定基础。演员,影像,还有舒伯特的音乐配到一起卓有成效,我是这么觉得的。

Q:是不是在准备和拍摄这场戏时已经想好要用舒伯特的钢琴三重奏了?
A:不,是在剪辑时定的。一开始,我觉得这片子只该用十八世纪音乐。但有时你会发现,给自己设条条框框并无必要,只会起反作用。我估计把市面能找到的十八世纪音乐大碟听遍了。很快就有了问题,十八世纪音乐没有悲剧爱情主题。所以最后我决定用舒伯特1828年写的《降E大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00号)。这是段美轮美奂的乐曲,对悲剧和浪漫的平衡把握克制恰当,不会像晚期浪漫主义音乐那样沦入过分感伤的滥斛。
Q:另外一处你也耍了花招,让Leonard Rosenman给亨德尔的《萨拉班德》重做交响配器,这个版本要比十八世纪版戏剧得多。
A:这里又牵涉到十八世纪音乐另一个问题——它也不够戏剧化。我最早听到亨德尔这段主题是个吉他版,说来也怪,它让我想到了Ennio Morricone。我觉得这段音乐用在电影里很奏效,简单的交响配器也让它不显得出戏。

Q:最后决斗——书里没这段——也用了这音乐,那是片中最惊人的场景之一,发生在鸽舍里。
A:那是个农用仓库,碰巧有很多鸽子停在椽上。大家在电影里见过太多决斗,我想给这场戏找点新花样。鸽子声给场景加分,这要是部喜剧的话,还可以再多给鸽子点戏份。总而言之,人们习惯看到电影决斗发生在户外,比如黄昏下雾蒙蒙的树林什么的。我觉得把决斗放在谷仓有股新鲜劲儿。这点子得来纯属偶然,有个外景勘察员带了点谷仓照片回来。记得是乔伊斯说过,意外是发现的门槛,至少在拍电影上的确如此。同样的道理,电影制作某种层面就像体育比赛。可以事先布置作战计划,但赛场上变化莫测,机会和困难应运而生,你只能随机应变。
举个例子,拍《2001漫游太空》时,好像没什么聪明办法,好让HAL发现两名宇航员信不过他,计划切断他大脑。要是他们大声谈论让HAL听到,那就显得太愚蠢。结果完美解决方法由太空舱在舰桥上这一设计布局自动生成。二人进了太空舱,把所有开关全部关闭,确保HAL听不到。他们面对面坐在舱内,镜头中部透过舱门隔音玻璃几十尺开外,HAL虫眼镜头的红光清晰可见。阴谋家们没想到HAL能读唇语。
Q:有没有觉得拍年代众人熟知的古装片更受限制,少了自由度?是不是挑战更多了?
A:不,因为至少知道每件东西是什么样的。拍《2001漫游太空》,所有东西都得凭空设计。但两种电影都不好拍。拍古装片和未来片,电影人的创作难度,和观众看到服装、场景、装饰的舒适感,两者成反比。一旦所有东西都得设计和打造,电影的花销就大大增加,所有电影制作的老难题都被加倍放大,现代片制作能办到的最后一刻变动,到这儿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Q:你拍电影前调查研究的细致是出了名的,是不是这样做有种当记者或侦探的快感?
A:是可以说有点像做侦探。为拍《巴里林登》,我收集了一大堆图稿和绘画的图片文件,都是从艺术书里找的。电影里所有东西都拿这些图片做了参考——服装,家具,手工品,建筑,交通工具等等。不幸的是,这些图片留在书上用起来太麻烦,恐怕到最后我们还是惭愧地从漂亮艺术书上扯下不少页来。幸好这些书还在出版,罪过就减轻点了。细致的研究是必须的,我也乐在其中。研究一项课题就必须钻得深,这很重要,立马就可以学有所用。所有戏服的设计都拷贝自那个时代的图稿、绘画。这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设计。我觉得,这是制作古装片戏服的最佳方案。拿着能直接拷贝的服装图片资料,再让设计师去重新诠释十八世纪,这么做不明智。它们已经在当时的绘画、图稿上美丽呈现了,再去修改也没什么意义。真正重要的是找些当年的衣服来,研究原始制作工艺。要看起来真实,就得用一模一样的制作方法。想想服装设计的品味问题,哪怕是今天,也只有屈指可数的设计师能把握住什么是引人的、美丽的。再伟大的设计师,又怎能像当年的设计师那样把握住那个时代的精髓呢?而那些都已由图片记载下来。开拍《巴里林登》前,我花了一年时间做准备,这时间花得很值。拍任何古装片或未来片的出发点及要素是让观众相信眼前所见。
Q:拍古装片的误区是沉迷于追求细节,变成花架子。
A:解决任何多元化问题都会有重一面轻另一面的危险,但我很清楚这点,确保自己不会落入误区。


Q:为什么喜欢用自然光照明?
A:因为我们平常所见就是如此。我以前拍片布光总想着模拟自然光;日戏用窗户来给场景真实布光,夜戏用景棚里的现有光源。在能使用明亮电光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已经有难度,等到棚内最亮的光源是烛台和油灯时,困难就大大增加了。在《巴里林登》前,这个难题从没正确解决过。即便导演和摄影师有心使用现有光源,胶片和镜头的感光速度也不够快,,没法正确曝光。一台35毫米摄影机快门曝光时间大约在五十分之一秒,要有镜头至少100%快过现用电影镜头才可能有效曝光。幸运的是,我找到一个这样的镜头,是蔡司为NASA卫星拍照定制的,总共才做了十个。镜头光圈是f0.7,100%快过现有最快的电影镜头。还得在镜头和摄影机上花不小功夫才能使用。比如,镜头后部到胶片的距离要确保有2.5毫米,得在旋转快门上做特殊手脚。但有了这个镜头,现就可以在暗到读书都困难的灯光下拍摄了。白天拍内景时,我们要么直接用窗户进来的真实日光,要么就是窗外打灯,在玻璃上贴描图纸来分散光线,好模拟日光的效果。这样不但能得到非常美丽的光线效果,还很实用。不必担心拍到电灯而穿帮。所有光源都在窗外,隔着层描图纸,直接朝窗户拍的话,会有种非常美丽且真实的闪光效果。


Q:为什么选了瑞恩奥尼尔?
A:他是这个角色最合适的人选。模样看上去对路,我也相信他有很大表演潜力还没挖掘出来。回过头看,我认为对他的信任完全得到了回报,我想不出有谁会比他更适合这角色。演员个人气质与角色是否相符,这几乎和表演能力一样重要。其他演员,比如说阿尔帕西诺,杰克尼克尔森或达斯丁霍夫曼,就举这几个伟大演员好了,让他们来演巴里林登肯定不对。我喜欢瑞恩,和他处得很好。我对演员要有意见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演技胜任不了要求。对此,演员的做法之一是发明些毫不相关的借口。特吕弗的《日以作夜》对此有精彩描述:电影里片中片的主角Valentina Cortese压根没练台词,却把念错词归咎于小场记造成了混淆。
Q:你如何看待一些英美媒体对这部电影的误读?
A:美国那边总体上在捧这部电影,时代杂志还做了个封面故事。海外媒体甚至更热情。的确,英国媒体对它褒贬不一。但打一开始起,我的片子就让影评人看法不一。有些人觉得很棒,还有些人找不出好话说。但到后来,评论观点总会很明显地倒向正方。举个例子,有个影评人一开始对电影加以指责,可几年后却把它放进了史上最佳榜单。但当然,一部电影的恒久魅力和终极声誉不在于影评,而在于多年来民众对它如何评价,有多大的热情。
Q:你是个革新家,但同时又很注重传统。
A:至少我在尝试吧。我觉得,二十世纪艺术的问题之一就在于过分追求个人观点和原创性,为此不惜牺牲其他全部。美术和音乐界尤其如此。这么做虽然一开始挺带劲,但很快就妨碍到任何特定风格完善发展,只体现出乏味无用的原创性。与此同时,很不幸的说,电影的问题正相反——大家都在不断尝试公式化和复制成功,一种风格尚未成熟就被抓着不放。成规是追求大众所想,原创性在这里就不着调了。现实就是这样,尽管历史反复证明墨守成规最危险。
Q:过去三部电影里,你完全摒弃了原创配乐。
A:照我说是摒弃了流行配乐。一个电影配乐师再厉害,也不是贝多芬、莫扎特或勃拉姆斯。既然有那么多过去和现时的伟大交响音乐可用,干嘛要用差一点的音乐呢?剪辑电影时,多试着配几段不同的音乐,看看是否与场景合拍,这很有用。这种做法很寻常。那么,多花点心思在上面,这些临时配乐可以最终成为定稿。我剪完《2001漫游太空》时,所有位置都安插了临时配乐——后来几乎全部用到电影里。然后,照通常的做法,我雇了个著名电影配乐师来写配乐。尽管他和我一起仔细看过电影,听到所有这些临时乐轨(斯特劳斯,利盖蒂,哈恰图良),也同意它们用得很贴切,可以作为每段戏的乐思参照。可他还是谱了、录了一版和之前所听截然相反的配乐。问题更大的是,我觉得他这版完全配不上这部电影。首映迫在眉睫,没时间重写配乐,要是连这些选好的临时配乐都用不上的话,那我就真没辙了。那个配乐师的经纪人打电话给当时的米高梅老大罗伯特奥布莱恩,警告奥说要是不用他客户的配乐,电影肯定赶不上首映档期。但这一次,就和其他时候一样,奥布莱恩相信了我的判断。他是个大好人,很少有电影老板能像他这样对电影人友爱忠诚。
Q:为什么用了电影里唯一那处闪回:孩子从马上摔下来?
A:我不想浪费时间描述这条故事线的全过程:小布莱恩从宅府偷跑出去,把马牵出来,摔下去,被人发现等等。我也不想仅通过抬着受伤男孩的农夫口述来描绘这场意外。在对话当中插闪回看上去最合适。
Q:镜头运动都是事先规划的吗?
A:很少是。我觉得在剧本里写镜头指示没有意义。只有想到些非常重要的镜头安排,我才会写下来。排练时,最好别去想摄影机的事。想了的话,我发觉总会影响到场景创意充分利用。等到最后有什么东西值得拍了,这时候再决定如何拍。有句话说当有什么真正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时,怎么拍不再重要,我觉得这话有道理但不完全对。任何情况下,安排布景、打光或镜头运动都花不了我多少时间。电影制作视觉的一面对我来说从不是难题,所以我会小心将它衬托到故事和表演下面。
Q:你喜欢独立创作还是与编剧合写本子?
A:我喜欢和带劲的人合作。我有过最愉快也最有成效的合作经历之一,是和阿瑟克拉克合写《2001漫游太空》的故事。电影剧本创作的矛盾之一,是真正能写的人不稀罕给电影写剧本,只有极少数例外。他们很正确地把重心放在著作上。《巴里林登》的剧本是我独自完成的。第一稿花了三四个月时间,但和我其他电影一样,随后的改写从没停过。写下来但还没拍的内容不可避免会受到拍过内容的影响。内容或剧力的问题会自行出现。一场戏的排练也能导致剧本更改。不管预先想得多细,好像觉得已经在眼前演过一遍,到了真正演的时候总不一样。排练中,或实拍中,有时会有全新点子凭空而来,好得没法忽视。这时候就有必要当场和演员排出新戏。只要演员清楚戏的目的,了解自己角色,这么做其实没想象中那么难,也要快得多。

注:原文在此
《发条橙》、《巴里林登》、《闪灵》三片上映时,米歇尔西蒙都为《正片》杂志做了库布里克专访
最后被集结到他80年出版的库布里克专著中
有趣的是,81年库还亲自把该书英文版访谈内容审核修改了一遍
via Ethermet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