铬黄、群青、胭脂红、泰尔紫、普鲁士蓝……熟悉油画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这些响当当的名字。
那关于他们的前世今生呢?
根据各类八卦艺术史所述——
铬黄含有大量有毒的铅,不少艺术家深受其害,譬如梵高与戈雅;
也有传言拿破仑死于翡翠绿壁纸中的砷中毒;

左:铬黄色调的《向日葵》,梵高,1888
右:大面积用了翡翠绿的作品《献给保罗·高更的自画像》,梵高,1888
胭脂红是从寄生于仙人掌中的胭脂虫中提取出来的,名贵得很;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的着色剂几乎都是药物,多从药剂师那儿买到;
已于1964年绝迹的“木乃伊棕”,真真是取材于木乃伊。

左:红衣主教身上的胭脂红,《阿格斯帝诺.巴拉维西尼画像》,安东尼·范戴克,1621
右:木乃伊棕的实际应用,《厨房内部》,马丁·德罗林,1815
还够不够八卦?接下来看点正经的。
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布希-唐赖辛格博物馆、亚瑟·M·萨克勒博物馆组成的哈佛艺术博物馆,墙壁里头可藏了2500种世界上最稀有的颜料。福格的前馆长,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爱德华·福布斯 ( Edward Forbes)收集了大量上了年纪的颜料来鉴定意大利的古典画作。

来自美国Baer Brothers的金箔粉。
在绘画中,画家通常使用近似于真金色的金属漆。但在基督教教堂的骶骨艺术中,也会使用黄金作类似“圣人光环”的点睛之笔。

来自英国Charles Robinson & Co.的珍稀印度黄(1914)
顾名思义,颜料产自印度孟加拉邦的一座小城。那儿的母牛仅被喂养芒果叶和水,因此尿液呈现亮橙黄色。印度黄就取自母牛的尿液,经过加热、蒸发、过滤、干燥后,被制成球状色素。这种惨无人道的生产方式在十九世纪被政府禁止了。
但不妨碍它是维米尔的最爱。

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仆》,1657–1658

已抛光的孔雀石。由其制成的颜料呈树叶般的翠绿色,被广泛用于化妆、壁画、制釉与玻璃上色。

来自龙血树的“龙血红”。名字很浪漫,但它只是一种藤类植物的树脂提取物罢了。
受传说影响,中世纪关于地狱、魔鬼以及各种事物的肮脏血液,几乎都使用“龙血”所绘。

来自西班牙的熟赭,1933
这位朋友,又叫氧化铁红,相信大家都挺眼熟——比如故宫的主色调,再比如消防栓的防锈漆。

人气甚高的群青,十四世纪时比金子还宝贵。
当时的原料取自青金石,产自阿富汗北区且只能由驴驮下山,再通过船运到达最终目的地。1826年,化学家终于发现了合成这种颜料的方法,才使得群青得到普及。
维米尔的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其头巾就是以青金石颜料所绘,五百年来仍旧鲜艳动人。

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1660-1665

埃及蓝,据说是人类最早使用的人工颜料。
在古埃及的信仰中,蓝色象征着生命、生殖力与重生,因此埃及人甚是喜爱上面那位天青石的颜色。但因其造价太贵,当地人遂开始绞尽脑汁制造合成颜料。这才有了埃及蓝,在当地语言中意即“人造的天青石”。

骨黑,煅烧猪骨提炼出的颜色,1933
由尚未炭化的骨头烧制,自带暖调,深受画家们喜爱。
这些颜料的过去,也被收进了独立出版社Atelier Éditions出版的“An Atlas of Rare & Familiar Colo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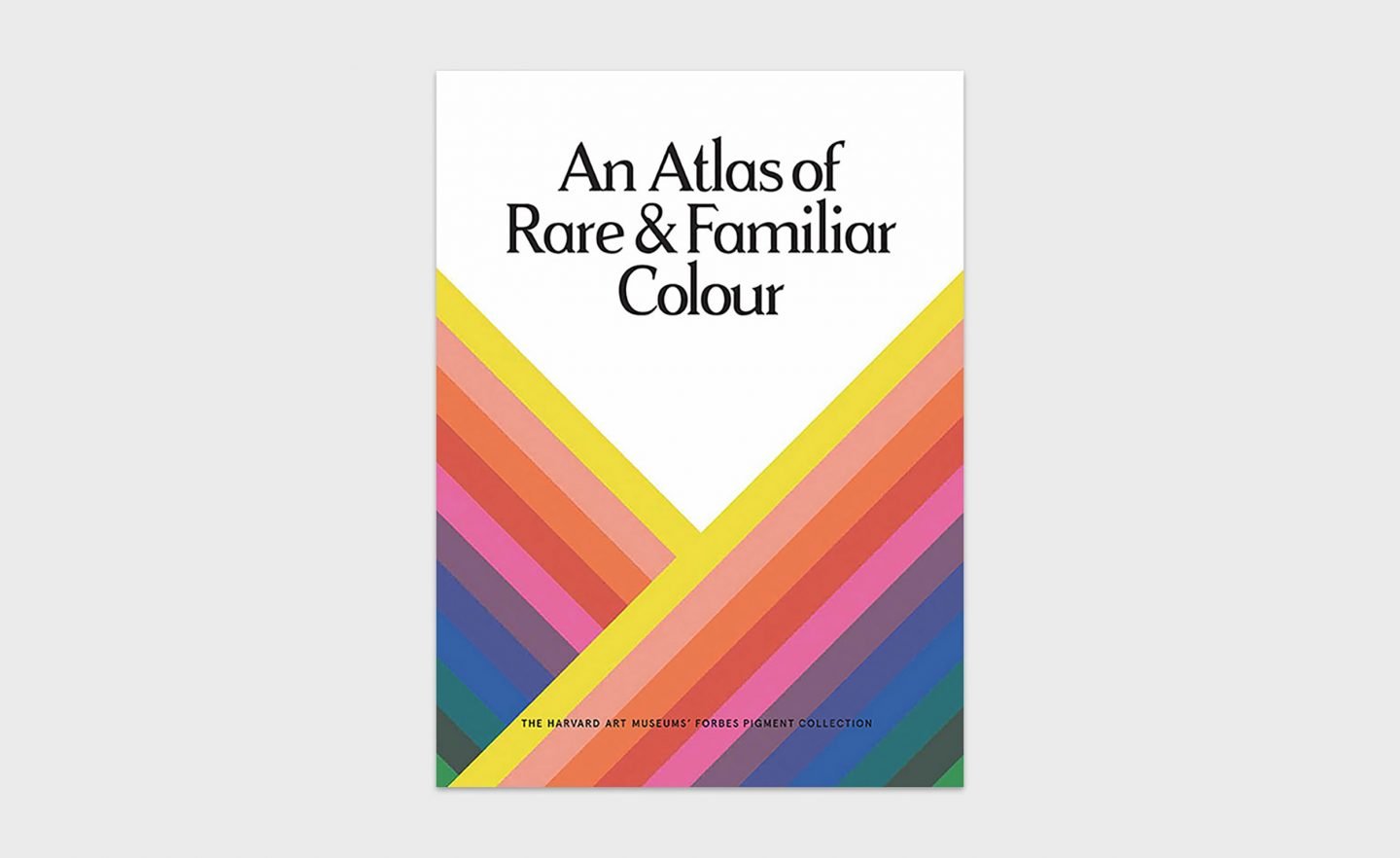


我们也许无法亲历那个画家们为昂贵画材省吃俭用四处奔波的年代,但这些会说话的瓶子,向我们倾诉着那些散在风里、淹在雨中的过往。
为如今我们能够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或是依然淹没在众多资料中的,热爱绘画的前辈们,致以最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