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手机行事历,你会发现它至少希望你填写两行的信息:标题(此时你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地点或视讯通话(你要去哪里、去干什么)。这是一个好主意,不用担心为了琐事或者越来越差的记忆耽误行程;但也是一种新型压迫:为什么凡事都需要落到“具体”?
这和乡村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问路得到的答案可能是“穿过两个山坡的后面”,亦或是某个山脚,桥上或河边——即便有路牌,大多也是为了描述眼前之景而形成的概括。这便为我提供了一个思路:为什么人们一说到「放松」便会界定到「远方」,要脱离城市,去到郊区、乡村或地广人稀之地?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具体”的娱乐场所、结构化的游戏、固化的体验,而渴求的一种可以发挥想象的、有弹性的“模糊”?
继而我发现,“垂直”的确会消解掉一些不期而遇的化学反应,正如1+1+1通常等于3一样。当知道了游乐园是游乐园,公园是公园,儿童区域是儿童区域时,我们便少了很多“绕远路”的乐趣。但是“好玩”可以是非目的地、全民性的、包容性的,作为城市的二次轮廓线,那些不能构成一个完整场所的、街道的附属设施也可以通过设计变得更好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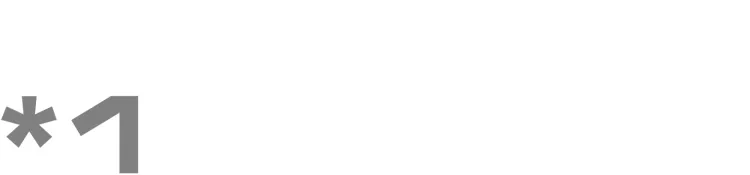
钟声响起,游戏开始了!
这当然是可以实现的,且有很多有趣的例子作为佐证。
谁都听过《灰姑娘》的故事,仙女教母送给辛德瑞拉南瓜马车、礼服和水晶鞋,但要她记住12点的咒语;《玩具总动员》的故事设定也是在夜晚或小主人安迪离开房间之后,玩具们会拥有自己的世界观。在“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的城市里,也有这样的魔法口令。
「A Playful City」是一个来自都柏林的奇特团队,由建筑、设计、法律、市场营销、城市研究背景的成员构成,他们动用了很多脑洞去开发各种年龄、文化和能力的人都能自由地混合、发展、联系的空间。在前期调研中,他们也倾听了很多人的声音,丢掉了一些刻板印象——譬如不是所有儿童都适合“儿童区域”(也许这只是大人偷懒的方式),不是所有儿童都有天然的、旺盛的社群意识。一位12岁的女孩Karen就说她不喜欢户外游戏,更喜欢呆在一个常去的游戏咖啡厅里。


如此,「A Playful Street」项目便应运而生了,通过与社区和当地警方合作,他们争取到了一个魔法——每天对市中心的街道临时封闭两小时,让所有年龄的人走出家门,一起玩耍。如果有人想要开车离开或进入这里,必须参考步行的速度,让位于玩耍。老人们可以借机展示跳房子等古老的游戏,孩子可以回归没有电子设备时期的街头玩具(足球、风筝)——在他们熟悉的街道、日常的风景,而非有固定动线的场所、人工的置景里。

无独有偶,抱着「去除游戏场所的不公平性」的目的、美国组织KaBOOM!也通过「Play Everywhere」项目,试图去打破城市游戏的结构化。他们认为,当下人们如果想要娱乐,必须去某个地方玩。因为家庭生活充满了麻烦因素,特别是对于某些生活在资源不足的社区家庭来说,一天中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玩耍,也无法在附近找到一个安全、方便的地方。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于是他们通过25年的努力,将美国许多地区的街道、人行道、公共汽车站、商业广场、停车场等17000个极易忽视的“沿途所见”,都变成了迷你“游乐场”。






大人们,一起来玩吧!
以上设计提供了一些将游戏融入日常生活,重新想象日常空间的方式。但也存在明显的标签,比如都是由点连成片的社区实践,又比如虽然强调全民参与,但依旧把“孩子”置于了本位。甚至于KaBOOM!明确表示过,最初打造这种非结构性的城市游戏空间,是为了给予处于社会弱势的“黑人儿童”公平的玩耍权利。
而对大人们来说,非结构性的游戏同样具有吸引力,甚至不需要借助严谨的游戏规则(因为大人早就明白他们多么擅长又多么讨厌制定规则)或是色彩丰富、夸张的外观设计,简单、重复、低门槛、原始的游戏场所更令人兴奋。而这就不得不说到以建筑工作室为主体进行的城市设计了,这类设计体量更大、技术要求更高、也更具实验性和公共性,除了好玩之外,还暗含了一些只有大人才能完全get到的意涵和野心。
Trampoline Bridge是巴黎的一座桥梁,但它显然和别的长得不太一样。AZC Zündel Cristea工作室认为,巴黎已经拥有了很多的人行道、车行道、水道和桥梁,足以应付日常的形成和常规的仪式。而一座配有巨型蹦床的充气桥,不光可以成为城市最独一无二的特色,也能让人们从重力中获得快乐的释放,去还原人类常常怀念和想象的那种原始的、幸福的状态。

这座“蹦蹦桥”直径30米,由充气模块+聚氯乙烯薄膜+内部弹力适中的蹦床网组成,通过绳索连接成一个稳定的自支撑整体。这个像巨型救生圈集群一样的桥,每个模块都充满了3700立方米的空气,因此形成一个拱形的奇妙弧度。任何人——如果你想的话,都可以经由它穿过塞纳河,或是尝试从以前不曾有过的独特视角观察巴黎,例如直立跳跃,倒立翻滚,像马戏团表演者一样滑翔…而它又如此邻近百年前变伫立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二者的位置关系也形成了一种“为城市带来幸福感”的回望,非常适合想从日常生活中越轨的成年人。


而2016年的蒙特利尔的音乐节广场(Place Des Festival),也出现了一个成功俘虏成年人、名为「心血来潮」(Impluse)的装置。它的制作团队是Lateral Office & CS Design,灵感来自Joy Division专辑《未知的快乐》(Unknown Pleasures)的专辑封面,以及Steve Reich的音乐(以重复、节奏和切分音为代表),试图以此探索建筑如何将声音可视化。

几乎所有路人都忍不住参与这个实验,因为它成功地激发了人们原始的游戏本能——这一互动装置由12个超大跷跷板组成,当两个人同时各坐一端,进行跳跃、起飞等动作时,系统便会发光和随机发出声音。这个装置后来被给予“改变城市沉闷街道”的愿望,送到了芝加哥、波士顿、斯科茨代尔以及纽约人来人往的服装区(Garment District),鼓励人们制作属于自己的灯光秀和音响节目。



游戏,未必需要开始与结束
简·雅各布斯曾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里写过一种关于“城市游戏”的心态: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玩的内容是什么,也不在于找一个正式的地方,正儿八经地玩。他们那种玩耍方式的魅力在于随处不在的自由自在的感觉,那份在人行道上跑来跑去的自由,这与把他们限制在一个圈起来的地方完全是两码事。如果他们不能做到随时随地玩,他们干脆就不会去玩。
诚然如是。在某一种标准里,似乎某个IP或是某类设施是否存在、存在的密度成为了判断“城市是否好玩”的重要指标。但是这种舍本逐末的框架,容易催眠我们,将游戏作为趋乐性行为的本质让渡于基于设计、包装的“成人意志”之后,因而“远方”那些非结构化的地标则成了我们称之为“好玩”的心之向往。
游戏,未必需要开始或结束。它可以像天外来物一样没有来历、不知起因地躺在街头巷尾,你可以以忘却规则的原始反应去驾驭它,就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