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的小说家都是会讲故事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即使置身于那一长串名单序列中,马伯庸仍旧是其中顶尖的说故事的好手之一,我想这一点也不会有人反驳。
马伯庸的故事受众有两批。一批人喜欢他作品中嬉笑怒骂挥洒自如的文字风格;喜欢他对史实细节的执着探究,反复打磨,精彩鲜活但绝不“忽悠”的呈现;喜欢他把恢弘的历史拉回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身上,又从“小”处去铺陈推展开宏大的时代背景和个体宇宙的充满人文关怀的观察视角和灵巧的叙事方式。
另一批人喜欢他的作品影视化之后呈现的“马伯庸风格”,《古董局中局》的亦松亦紧的轻喜剧叠加悬疑的氛围,《长安十二时辰》快节奏的多线叙事、层层堆叠的矛盾和反转最终带来拨云见日的酣畅快感,《丝绢案》将细琐枯燥的史实细节融入到人物特质和情节推进之中,让观众既感受到看故事的愉悦又有所收获和思考的双重魅力。
说得更直白一些,看马伯庸的历史小说,会觉得既快乐又安心,因为这是一个有趣又有料的创作者。
抛开这些感性的描述,马伯庸又是一个坚持创作十余年、新作不断地勤奋写作者,是一个被市场、大众和专业人士同时认可的成功创作者。他如何看待历史和当下的关联,如何把个人兴趣变成一份安身立命的志业,如何在激荡变化的内容潮流中找到和坚持鲜明的个人风格,在《丝绢案》热映余波未散,新作《大医》巡回签售的间隙里,我们采访了马伯庸,抛出这些问题,得到了一系列真诚准确、掷地有声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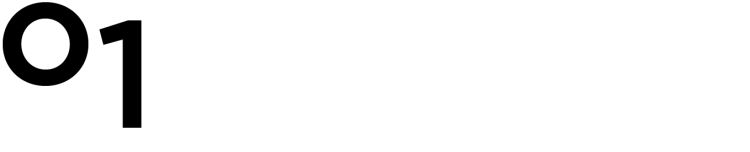
说好一个故事
TOPYS:看一些消息称您去年的作品《长安的荔枝》也在拍摄当中了,预计也会在今年和观众见面,这部剧您有参与制作吗?原著中,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和《丝绢案》里的帅家默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人都精通算学,是那个时代难得的“理工科人才”,但又都因为种种原因很难被体制认可活得比较边缘,再比如帅加默这个故事背景是明代的徽州地区,您在《长安的荔枝》的前言里面也说到主角的人物原型是徽州籍贯的一个小吏。

所以,您近几年好像越来越喜欢写那些历史缝隙里的小人物的故事,但您的操作手法又是用非常恢弘的视角把他们的人生写得很有滋味,甚至很开阔。这其中,就有一种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的评价机制的分割,一方面他们还是小人物,但另一方面,他们有自己发光的舞台,可以说是平凡而伟大的。这算不算是一种给当下读者的安慰?还是您觉得这其中也有历史和人生的真相在?
马伯庸: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坚定的史观:所有的历史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些人民群众单一个体是无力的,也很容易被历史长河湮灭掉他们的声音。但是当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人聚合到一块,他们形成的需求,就是所谓的时代之潮。那些英雄人物则是顺应这个潮流站在潮头而已。所以说白了,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会知道长江是往哪去的。
我这几年越来越把兴致放在这些事务性内容,写小人物干活。干活的人是最难的,所以我很有兴趣探讨这些人怎么干活,干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说白了,我们都是社畜,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些问题,古代人也有这样的困惑和麻烦,那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该以怎样的哲学观去理解?
我曾经看过一个有关三国志的展览,里面展览的是所有跟三国有关的文物,我在那儿看到了两块砖。
第一块是在安徽亳州的一个墓葬里面发现的砖头,时间是黄巾起义前14年。这个砖头上有一段工匠写的话,大概意思是“你们快把我逼死了,现在我就等苍天已死的那一天,我要跟你们算帐”。看到这块砖,你会一下子明白,为什么黄巾起义能够席卷天下。在黄巾起义的14年前,这些基层老百姓中,一个最普通的烧砖的工匠,已经被压迫得走投无路了。他喊出这种话时,一定有千千万万个跟这个工匠一样的人,同样受着压迫,同样在内心燃着怒火。
当这么多人都产生了“我要跟你同归于尽,我要跟你好好干一场”的心愿,最后就形成了汉末的历史趋势,才有了曹操、刘备、孙权这些人的趁势而起。
另外一块砖是在以前吴国的首都建康旁边出土的。当时晋国灭掉了吴国,天下已经三分归一统,这块砖写的就是“晋平吴,天下太平”。我考证后得知,这块砖的主人大概70多岁。三国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这位老人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战乱,一直到他70多岁,终于看到了天下太平的曙光。我想战争期间,就算他不上阵打仗,他的朋友、亲戚也可能被战乱波及,他自己也可能要承担极其繁重的负担,现在“终于天下太平了,不打仗,可以安心过日子了”。那时一定有千千万万像这个老人一样的老百姓,他们已经无法承担战乱的结果,当他们一起呼唤和平的时候,天下三分归一统是必然的趋势。
这两块砖当时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感觉——它们解释了三国乱世的起源,和三国乱世的终结。我们看到历史的主角,并不是那些名将、谋士、王侯们,而是这些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人,他们的需求最后会形成历史趋势。这是我对小人物的理解,我就想写这样的人。

TOPYS:您曾经自称“知道分子”,从“知道”中获得灵感,到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再到细致打磨完善细节,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或者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吗?例如,您一般会先有一个创意核心/主题立意,再去安排时代、人物、情节呢,还是您会被某个朝代、某种地域文化气质或某个不起眼的人物原型刺激到,再去发展出一个故事的内核?就您的体验来说,要完成一本书的创作,是充满意图地设计一个故事更重要,还是水到渠成的“下笔如有神”更重要?
马伯庸:我特别喜欢从一个细节入手去挖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样能挖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这和我的创作习惯有关——英国作家弗·福赛斯的间谍小说里面有大量的细节,让我觉得很酷,这可能是我着重描写细节的创作源头。写细节的前提就是要去查大量的东西,要保证细节是准确并且有用的,这就要深入挖。这个习惯养成之后,我经常会花一天的时间挖一个看似没有关系的事,挖完也没有什么后续的动作,就是挖的过程很开心。
至于说写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中二的态度。所有的创作者一定都是不成熟的,当一个人足够成熟之后,他就不想创作了。就好像一个老禅师一样,已经人淡如水,看清世间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看不破世界,你才有想表达的东西。一个人只有正在经历世事,有愤怒、有情绪、有遗憾、有兴奋,他才能成为作家。归根到底,作家是靠荷尔蒙写作的,如果没有激情的话,写什么都没劲了。
TOPYS:您写作已经很多年了,近期作品中,除了不同主题,有没有做过其他新的尝试,比如细节的描写,或者尝试不同的语言风格?
马伯庸:其实我的每一部小说的文体、文笔都会做一些调整变化。像《古董局中局》,更接近民间的故事,用口语化的传达大家会觉得比较合适。写《长安十二时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迅速的反恐故事,我就尽量用短句子,尽量用精准的描写制造出一种节奏感和速度感,而不是去过度地铺陈氛围。《两京十五日》我就把速度和文字的厚重感放回到明代的那种感觉。再后来到《长安的荔枝》又回到盛唐的那种雍容。
核心来说,我会很关注我的书读者是一口气看完,分两天、三天看完,还是根本看不下去。对于叙事的流畅度和阅读的动力,我还是挺关注的。这个大概是在写《古董局中局》的时候开始的,第一因为这个作品和我之前写的不一样,它是一个破圈的,算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第二,我写它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风,刻意用了一种说书人的口语化的表达,所以你会看到里面的话特别顺、特别溜,它不是文学的表达,更像是一个人的口述史。这也是我的一个尝试,原来太过于雕琢句子的复杂程度和巧妙程度了。而当我明确了是想要一本畅销书的时候,口语化对于降低阅读门槛就是很重要的。那本书出版之后很有意思,很多老读者会问,你这本书是不是代笔,怎么跟你风格不一样?但是放在家里,他们的爸妈拿过去会一口气看完。你会发现这么写之后它触及到了更多的读者。但是后来我又及时拉回来了,我觉得一旦养成习惯了,就麻烦了。
因为语言的门槛降低之后,首先损失掉的就是信息量,口语带来的信息量是不够的,尤其对于细节的描写。虽然写的时候是很畅快的,但这种畅快是很危险的。习惯了口语写作之后,想回到正常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就好像天天写口水词,写多了之后忽然让你写一个高雅的东西,整个人就会找不着感觉。所以后来我也不执着于某一种文体,而是用适用于主题、故事的文体。
但是我不可能去吸引所有的人,不可能说比如现在市场流行言情文学,我就去写一部言情,我也写不了。我擅长写的还是在历史悬疑或者历史解构这方面的东西,那就只能通过自己比较有特色的表达方式,吸引一批跟我志趣相投的人,做好市场细分就够了。市场上历史作品始终就不是一个主流,因为读历史作品首先要有一定阅历,也要有一定的文史基础,这对大部分很多人来说是个很累的事,尤其是这个时代有这么多吸引人的东西,剧啊、电影啊、游戏啊,都是比书更容易吸引注意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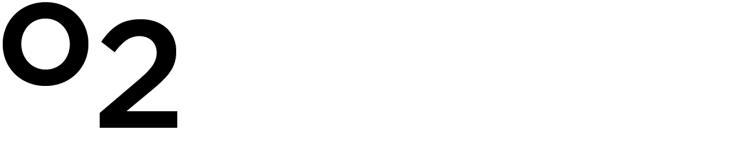
作品影视化与马伯庸宇宙
TOPYS:今年三月《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上线了爱奇艺,您的名字被放在了总编剧的位置上,这是您第一次以编剧身份参与到作品的影视化过程中,您觉得写剧本和写小说技法上的差异巨大吗?第一次编剧有什么有趣的新发现?
马伯庸:我写完剧本之后,对于编剧的尊重和敬畏更深了一层。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情非常难。并不是说你会写小说了就一定能当编剧,也并不是说你会讲故事了,做编剧就能写出来。实际上从故事到剧本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真正的编剧,要考虑的事情也不仅仅只是故事本身,他还要考虑演员的状态,考虑到拍摄时候的东西,他要把所有这些事情都考虑清楚,写成一个能够让后续的这些加工环节能够发挥出功能,能够让这些演员有足够好的平台去表现出来,编剧的责任非常重大。
一直以来我都是把影视剧的镜头技法放到小说中去,所以很多人会问我,“是不是为了方便以后影视化改编,才把小说写得特别有画面感?”我想说这是两码事,画面感归画面感,这是我从影视剧里学来的,但是不代表它就是剧本。你写得再有画面感,到了剧本阶段你还是会把这一切推翻重来。因此,作家既要能够从影视作品中汲取经验,也要能退得出来,不能完全被影视所束缚住。

TOPYS:“大明”这个系列有6个故事,为什么最先将“丝绢案”搬上荧幕?“剧本首作”为什么选择奉献给这个故事?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参与其他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大明系列的其余几个故事也准备做影视化呈现吗?
马伯庸:本来我是不想做编剧的。一开始我说给编剧做培训,把我知道的讲给他们听,后来发现要讲的太多了。这次比较特殊,不单是要从无到有起一个新故事,同时也要把丝绢案整个事件的精髓保留下来。我想,这事那么难,不如我先试试看。
《显微镜下的大明》原作里是大量的会议记录和辩论过程,没有我们熟知的起承转合这种戏剧性结构。史料记录下来的是丝绢案这件事,但影视剧需要一个故事。主角是帅家默,程仁清这些人,那么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动机,包括当地的这些县官,每一个县官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把这些人梳理起来,抓住他们的典型,然后组织成故事,转成一种可视化、可听的东西。这很难。不光是我,包括导演、演员,还有音乐、灯光等各个部门都是群策群力,尽量让这个过程变得生动有趣。
比如说丝绢案里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这个丝绢税应该怎么分配,它的矛盾在哪?这个东西要讲清楚,至少得两页纸。但是观众不可能有耐心听你讲半个小时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也不可能通过那么短的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细节,就是主角给县里的这些官员讲,给县里老百姓讲,包括给丰宝玉丰碧玉讲,他们也听不懂。那主角逼得没办法,就在墙上画了一个示意图,就有点像现在写ppt一样。那么就通过这么一个镜头,就是把这种听觉讲解给它变成了一个视觉呈现。这个对于观众,至少说你如果愿意定格看的话,你是能够理解这个事,你不定格看一闪而过,也不影响这个剧情的推进。
但另一方面,在考虑戏剧性的同时,我们还希望能保留一些真实的质感。这个真实,不是指历史上这件事情真实发生过,因为这不是一个纪录片,影视剧要讲故事嘛,肯定是要有杜撰的部分。我追求的真实质感是人物的行为能符合当时的社会逻辑,换句话说,我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啊,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在当时发生过,但是它有可能发生。这个人没有做过这件事,但是他真干得出来。符合这个逻辑,那么这个故事才能够成立,才能够让人信服。
开玩笑的说,他们能让我把这个戏写完,同时把它上线播出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剧播后,看到观众讨论很热烈,剧的热度也很高,我觉得算是幸不辱命。
后面《显微镜下的大明》其余5个故事也会继续开发,会有更多优秀的创作者来合作完整作品的影视化,期待这个系列有更多更优质的艺术作品,展现给每一位观众。“丝绢案”算是我作为编剧为系列作品打了一个样,我个人的编剧生涯大概就到此为止了。
TOPYS:电影有所谓的类型片,随着您的名字与前面所说“历史缝隙里的小人物故事”越来越多地绑定,您是否会觉得自己也渐渐成为一位“类型化”的作家?如果是的话,您会怎样定义自己的“类型”,如果不是,接下来在历史中的微观故事之外,您准备开拓什么样的新领域?
马伯庸:作家之外再画一个大圈的话,应该是文化圈。因为我对历史类的、文化类的、尤其是传统文化相关的主题也做一些研究,也没有给自己限定是个什么身份必须做什么。就像一个作家不可能只读文学类的书,一定是兴趣扩展到更宽的领域,才最后形塑成你的作品。

TOPYS:除了影视改编,您对人们所说的“马伯庸宇宙”的新版图有什么规划吗?除了您本人的智力创作以外,这个宇宙中最重要的一些要素您认为是什么?
马伯庸:我其实一直比较回避“IP宇宙”这个事情,因为一旦形成这个想法,就会对创作产生影响。我还是希望写作比较纯洁一点,只是说写出一个我觉得好看的故事。如果后面机缘巧合,有人愿意改编,把它改成其它的艺术形式,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了,但这不会构成我创作的最主要的动机。对我而言,分享是一种本能,写小说就是把我想到的,我感兴趣的东西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的过程。我就是个写小说的,完成作品是我的本分,至于其他,都属于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而且,宇宙这个东西是彼此关联的。你会发现我每一个作品,其实跟我的其他作品都没有关联。我会一直刻意回避彼此之间的联系,尽量让它们变成各自独立的作品。我一直很担心被读者抛弃,所以希望每一部作品都能带给读者新鲜感,这样读者才不会看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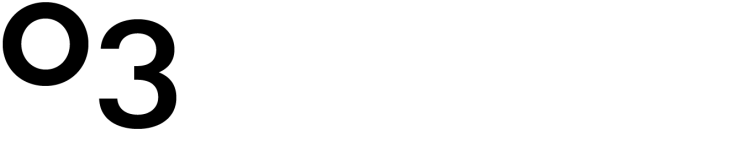
“灵感就像猫”
TOPYS:您工作时,对时间、地点、环境等外在因素有没有要求?从兼职写作到全职写作,中间的状态转换顺利吗?有没有情绪震荡期?在情绪不够平稳或者故事推进不下去的时候,您一般会做什么事来找回状态?
马伯庸:因为做过⼀段时间的上班族,我养成的第⼀个习惯就是⽩天写作,早九晚五跟上班⼀样,回家之后就不写了,把⻔⼀关进⼊休息状态。
第⼆个习惯是我必须在特别吵的地⽅。以前上班的时候都在⼯位上写作,周围打电话呀开会呀吵架什么的,我就习惯这种环境了。
有⼀次去杭州⻄溪,朋友给我提供了⼀个别墅,说可以住三天。那别墅⾮常好,也很漂亮,屋⾥开着空调,放着⾳乐,有茶有酒,什么都有。结果三天⼀个字没写,光在这玩⼿机了。时间到了我要回北京,提前三个⼩时到萧⼭机场,坐在登机桥前⽂思泉涌,⼀⼝⽓写了⼤概3000到4000字。
灵感就像猫。你越想去抱它,越想去抓到它,它跑得越远。但是你不搭理它,你就专心做自己的事,它一会就到你脚边来蹭了。

TOPYS:去年下半年,您有三部作品出版,再往前看,您也几乎是每年都有新作品面世,如此高效率创作的秘诀是什么?比如,您是规定自己每天都写吗?
马伯庸:其实这是一个误会。从2017年到现在,从《长安十二时辰》到《两京十五日》,再到《大医》,真正的长篇只有三本,字数加在一起也就一百多万字,也并没有多少。在这几本书的中间,我写了几个短篇,但那字数就更少了。平均下来的话,大概一年能够保证有一本书出版。跟很多作家比,我这已经算很低产了。
写作和别的工种不一样。就算再讨厌搬砖,你咬着牙搬,每天搬300、400块砖,你也是有收入的。但写作无法强迫,如果你写得特别难受,完全为利益驱使而写,坚持不下去。写作是非常诚实的状态,完全无法隐藏作者的好恶,只有喜欢才能走得远。
作为创作者,一定会有才思枯竭的那一天,这是所有写作的人都无法避免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但现在还没有来。写作对我而言,还是一件很快乐的事,那我就要趁现在赶紧写。这是非常关键的,只要还喜欢,是兴趣所在,还有想写的东西,就一定会忍不住去打开文档。
TOPYS: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利用网络锻炼自己写故事的能力 ,为全职作家的职业规划铺路,如果想加入这个行业,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冷水”?
马伯庸:先找份工作,找个班上。我现在觉得作家不是一个身份,作家是一个状态,当你有冲动表达一些东西并且付诸文字,你就是一个作家,当你写完把笔记本合上,你就不是作家了。每个人都有几个瞬间会是作家,作家也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很多人没有作家这个身份,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很好看。

我们第一次联络马伯庸,他正在新书《大医》巡回见面会的途中,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几经周折才最终敲定了采访时间。而在采访的同时,他又已经踏上前往东北和书迷见面的旅程。新书分享会或者书迷见面会,曾经是创作者和书迷朋友能够面对面交流分享的重要渠道,如今仍旧坚守这一形式的创作者越来越少,马伯庸却好像对其中的奔波辛劳甘之如饴。
他擅长表达,似乎也喜欢表达,从他在社交媒体上毫无包袱的日常分享、玩梗吐槽、“抖机灵”或严肃的文字分享,就能看得出;但在采访完成之后,我们发现那个社媒上“3D”立体呈现的马伯庸不是他创作的核心,回归到写作上,他克制、严谨,表现出创作者面对创作真诚而严肃的一面。
相比于有典型“作家人格”,对人群避之不及的写作者,马伯庸又更坦然自如,我想这和他透过作品呈现出的历史观(同时也可视作人生观、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不无关系。他看到了“小人物”身上的华彩和光芒,看到了他们身上鲜活而充实的生命力,他自己也不惧怕成为这样的“小人物”之一:做着喜欢的事,讲着喜欢的故事,不疾不徐地坚守一些东西,其他的顺其自然。这很“帅家默”(《丝绢案》主人公),这很“李善德”(《长安的荔枝》主人公),也很马伯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