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长的季节》已经进入长尾效应阶段,相比于热播时期的一片叫好,社媒上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一篇题为《逆风吐槽<漫长的季节>,这漫长的爹味》的文章引发了对该剧“爹味与否”的争论。讨论本身是件好事,只是在短平快的社媒阅读语境下,很多原本可以形成良性交流机制的讨论,都不可控地滑向情绪化的骂战,让人惋惜。
因为看过太多类似的例子,知道在社交媒体这样相对去中心化的舞台上,达成全部人的共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说什么都会有反对者),所以在开头就替一些最看重结论的朋友先提供问题和非常私人化的回答。
“说这么多,到底该站哪边?”
如果是我的话,不喜欢看一个剧大概就不会把它看完,因为吐槽本身不如我的时间和精力宝贵(有合理目的另当别论)。不喜欢某篇新媒体文章呢,我会沉默甚至取关,但不会举报或在评论区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这本身不解决问题,消灭某种声音甚至试图消灭发声的人,都是基于暴力逻辑,而非交流所需。作为单纯的读者或观众,如果发觉接触某些内容会消耗自己的能量,让原本艰难的生活更添一层阴霾,请大胆地绕开,要知道寻求安全感(无论是情绪的还是身体的)是人性常情,并不是逃避或懦弱,也无需为此羞耻。

说回《漫长的季节》,在后续的舆论风暴中,“爹味”显然是那个暴风眼、引发争论和分歧的源代码。但在批评派高举女性主义大旗和拥护派抨击女性主义站位的极限拉扯之中,唯独“爹味”到底如何定义,它被放在规范化的文艺批评语境中是否合理,说某部作品“爹味重”能否有效引起观众和创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促进一些积极的改变发生,这些关键问题却都有一点被避重就轻的嫌疑。
而这些问题的背后,还可能牵扯出一些更让人纠结的问题,比如,女性主义该如何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实践;是否所有创作都难逃接受某种意识形态拷问的命运,而这又是否合理;要求弹性的话语空间是否等于与既得利益者同流合污;两性之间能否通过心平气和的沟通达成某种程度的动态共识; 应该如何警惕和应对新媒体语境场之下的语言膨胀,如何让固化的立场和主张流动起来,形成有益的公共话语空间;等等。这些庞大的问题大部分都无定论,但每个人都不妨尝试思索,形成自己的见解。
基于以上,本文也力有不逮,只能回到具体而微的讨论语境,争取在符合理性的范围内探索一二,观点中庸,对一些人来说约等于无聊,如果不符合您的口味,只能遗憾地建议您到此为止,去看点刺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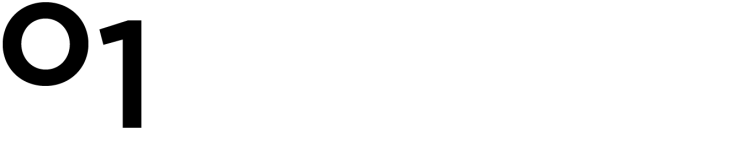
一个表达者,怎样去“爹味”
很容易搜索到的信息是“爹味”也是个舶来词,由英文合成词的“mansplaining”翻译而来。mansplaining在2010年被收入《纽约时报》年度词汇榜,原初定义是“男性以一种居高临下、过分自信的态度和通常是不准确或过分简化的方式,在女性面前评论或解释某事。”
而在词义可以自由外溢的互联网语境下,爹味有很多种似是而非的模糊用法,大多指向一种说教而非交流的对话模式。交谈过程中,某一方一味以经验、学识、社会资源等权力优势占据交流主导者的位置,不顾另一方诉求和想法,通过自我输出以求自我复制和自我经验的平移,达成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爹味更像是处于分享和煤气灯效应之间的灰色地带,算不上纯粹的邪恶,但确实让人不适。

假设以上描述还算准确,我们回观现实生活中的点对点交流,这种“爹味”可以说随处可见。理论框架内它是一种权力结构不平等的产物,理应不拘于特定的性别和年龄段,但落到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在东亚社会,用“爹”这样性别特征显著的字眼来组织词汇,的确显得更普适,更贴合社会现实。但是是否,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种抽象向具体的妥协本身就隐含着风险,一种语言所代表的丰厚意义被现实简单过滤、成为单维标准的风险,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每一种言说,实际上也是另一种遮蔽。当我们保有这种警觉,语言的弹性会衍化出意义和价值观的弹性,才会通向我们希望看到的多元丰富的世界。
说回到《漫长的季节》引发的讨论,以及对创作是否应当接受爹味审查的思考。创作者同样也是表达者,而公共领域的批评者同样也是言论的创作者,两者都理应保有创作和表达的自由。说得更直白些,辛爽大可以对批评的声音置之不理,继续拍他擅长讲述的父辈故事;而萝贝贝也大可以继续批评下去,不管所谓“评论区里男宝的声音”。在这样的舆论场里面,有鸡蛋和石头之别吗,在我看来并不存在,双方都是石头。
而鸡蛋又是谁呢?它可能不是具体的个体,而是我们当下社会本就脆弱和不堪一击的共识基础和理性思辨能力。它也可能是具体的个人,具体到如你我TA。
如果说爹味的本质是一种权力结构的不平等,那对抗爹味的有效工具是什么?我想不是急于给出结论、获得拥趸,看两方争斗不休。而恰恰是合理的诉求,有效的沟通,以及尽量理性平实而非煽动性的表达,还给每个个体以独立思考和评判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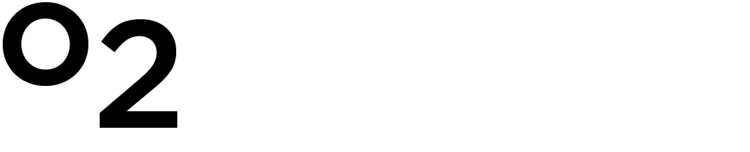
不完美的作品有没有其他批评维度
本质上,创作者在创作时候并不一样都带有是否爹味这样的自觉,其出发点或是讲述自己擅长和熟悉的东西,或是创作市场喜闻乐见的内容,《漫长的季节》我们可以推测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前者出发,创作者在力有不逮时扬长避短无可厚非。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否让所有观众都满意,也无可厚非。创作者的自由在于可以选择性地吸引有共情的观众或读者,而读者或观众的自由也在于可以选择被吸引或拒斥。在文娱作品泛滥化的市场环境里,可选之作太多,如果不是强迫每一个观众接收自己的表达,进行填鸭式地灌输,我想大可以不必评价创作者“爹味”或者剧集本身“爹味”,这种表达除了引发部分人的不适,放在批评语境里,还不如表达「其中某个具体角色有爹味,令人反感」来得更高效、准确和清晰。
而故事或者说文学这种创作形式是否可能承载“爹味”这么艰巨的任务(说教),也值得怀疑。
故事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分享几个给过我启发的观点。
作家和书评人唐诺有过这样的表述: 在这个具体的人被资本和技术吞噬、不断消失的世界里,只有文学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个体,让每个人以个体的意义具体地存在着。
2022年,石黑一雄接受纽约大学《华盛顿广场新闻》采访时说到:当我们给对方讲故事时,我们是在交流情感,以及在某些境况下的感受。我们建立共情。即使某人的观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但理解人们为何这么想非常重要。当此刻的世界有如此明显的分歧时,我们必须小心地创造唤起情感的故事,以确保与真相有某种关系。
两种观点都指向文学或故事的弱功利性。一个再好的创作者也无法创作出完全正面或完全负面还能走入观众内心、获得情感共振的人物角色,本质上创作者的诉求不是宣讲任何观念而是寻找共情。就像《漫长的季节》创造王响的角色,既不是为了让观众感受到“伟大的父爱”,亦不是因为他爹味十足,而是因为这个角色的功能性——即创作者希望表达的宿命感和人性的执念与温度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张力,这种张力至今还可能会引发一些人的共情。
《漫长的季节》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有没有问题呢?的确有。
美素、黄丽茹和沈墨,这三个女性角色身上呈现了三种不同程度、递进关系的女性自决。美素跟儿子王阳的一段对话既是在向儿子解释父子间冲突矛盾的原因,同时也带着自我剖析的意味:“我们这代人被安排惯了……我们这辈子就觉得自己身上是有个圈的,我们就按部就班地在圈里走着,也没人问为啥,也没人到圈外溜达过,就连踩了个线都害怕。现在这个世界变化就是快,哪代人都有哪代人活法。”但这种模糊的认知还不足以支撑她在现实中去改变什么,她还是那类传统的、围着家庭转的母亲形象。

黄丽茹不同,九十年代末轰轰烈烈地恋爱、婚姻危机时果断提出离婚、经济上相对独立,她并不是“循规蹈矩”、活在别人设定的圈里的女性,在恋爱关系和事业追求上都有一定的自决能力,似乎更贴近当下大部分女性的生存常态,因而也是成立和能够让人共情的。
在这样两个相对有现实感和立得住的女性角色映衬之下,这部剧的绝对女主沈墨却刻画得相当粗线条,让人觉得似曾相识,丝毫没有惊喜。沈墨并不是生活中常见的女性,她是个受害者,同时也是个愤怒冷漠的杀人凶手,从受害者向施害者的转变的过程本应是这部戏的重头戏之一,相比于外部情节推动,人物心理动机的逐步转变和形成更能决定这个角色是否可信、是否能够被理解。
可惜的是,李庚希塑造的沈墨并没有获得这种人物弧光。导演安排了一场戏来解释沈墨如何产生报复的念头,但这场戏怎么看都有些潦草——音像店遭打砸,弟弟傅卫军受伤,王阳被赶出维多利亚后跑来找沈墨,沈墨拿着药走进来,平静地一边交代音像店发生的事,一边给弟弟擦拭伤口。这时候突然停电了,王阳抱怨了一句“我们三个恐怕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前期没有任何情绪铺垫的沈墨却突然发狠道“倒霉的应该是他们”,且不说套路的情节真的太像我们在各类复仇情节中经常看到的桥段,连台词都是空洞的,没有展现人物内心的力量和澎湃,甚至都不符合沈墨一贯隐忍的风格,她没有在楼道里偶遇殷红时产生杀机,没有在看到弟弟受伤后情绪崩溃,却因为一盏电灯的熄灭而动了杀人之心,着实有平地起高调、令人跳戏的错位感。

第一次杀人,要求沈墨突破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恐惧,杀人者和被杀者的对白行动都应该服务于沈墨突破道德底线、被激发出邪恶力量的一瞬,此时产生的杀人动作既是观众情绪的出口,也是沈墨的后期人格成立的关键,但导演甚至没有交代具体的杀人过程,只用王阳的视角带到了卢文仲的死,沈墨则是木讷地交代了简单的事实“他死了”。镜头切换,王阳问沈墨为什么非要杀卢文仲,沈墨绕开话题,让这个问题成了观众只能去猜测演员和导演意图的谜题。但沈墨擅自行动置三个人于险境、事后甚至没有交代的表现难道不会损害团队信任吗,这样的情节处理还能支撑得住傅卫军和王阳一个替她顶罪、一个替她赴死的结局设定吗?
相比之下,连反派的女性角色殷红都能用为数不多的几场戏被记住。她可以对比她年长和弱势的巧云施以援手,也会嫉妒年龄相仿但看似人生圆满的沈墨,这不是角色的横跳,而是人性的复杂。在灌醉沈墨之前,她的大段坦白,在通知卢文仲来接沈墨之前,她的纠结犹豫,都赋予她的每个行动在角色预设框架内的合理性,甚至让人共情。
所以说《漫长的季节》“目中无女”,倒不如说辛爽的确没有创造出一个人物丰满生动且令人信服的女主角。
《漫长的季节》的确并不完美,嫁接了太多浪漫的元素在一个颇为现实的题材上面,给人高举轻放之感,影响了表达的深度,至于太多的救赎都给了男性角色,我想这是创作者能力所限的结果,但也是创作者的自由。也可以说,文学存在的意义就是呈现具体复杂的人性和它背后参差的个人生活世界,而不必成为任何理念宣教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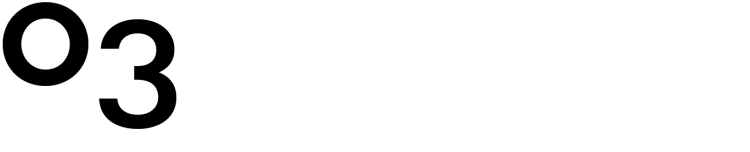
讲好“鸡蛋”的故事
在鸡蛋和石头的比喻里,鸡蛋是弱者的象征,石头是权力的象征。
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提出,女性主义绝不是弱者试图变成强者的思想,它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
正如我们提到过的,在每一场搅动公众而没有具体受害者的言论风暴里,都不存在鸡蛋和石头之分,大部分情况下双方都是石头。所谓交流看似是表达诉求,实则更多的是情绪的发泄;所谓捍卫女性,实则也并没有出现任何具体的女性。只有在现实中才存在大量的鸡蛋和石头的对撞,被家暴的女性是鸡蛋,被性骚扰和侵害的女性是鸡蛋,被当成商品交易、用链子锁住的女性是鸡蛋,被生育功能困住的女性是鸡蛋,被搅进言论的迷宫、失去方向、失去对世界信任的基础、失去理性思辨能力的女性也是鸡蛋。鸡蛋可以出现在任何不对等的交互语境中。

一个男性创作者如何讲好女性的故事,不妨参考刚刚过世的万玛才旦2019年的作品《气球》。《气球》中的藏地女性卓嘎受困于家庭、社会现实、父权期待和信仰交织冲突的困境,无法自决是否要生下意外怀孕的婴儿。基于深刻的共情和对素材的熟练掌握,万玛才旦讲出了女性真实的具体的困境,但这样的机缘无法强求。
女性观众也无法逼迫一个不熟悉或没能力讲好女性故事的男性创作者去做这样的迎合,而只能寄希望于两性之间有更多的情感共振和女性创作者的自觉。但是,不能讲好女性故事的创作者该被舆论绞杀吗,或者从其他维度讲述人类困境的作品没有存在的价值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在这种语境下,哪一方又成了鸡蛋。
从女性视角出发去观照社会现实也无可厚非,但在最近引起热议的“女生污蔑大叔偷拍,曝光其肖像并进行不当评论”这类新闻事件中,谁是鸡蛋,谁又是石头呢?
女性主义原本可以帮助更多女性达成意识的觉醒,有效和理性地规避伤害,降低伤害造成的身心层面的负面影响,从而帮助个体根据自身情况差异化地突破性别身份困境。但将一切都和性别压迫捆绑,造成两性的尖锐对立而非良性沟通,将情绪发泄包装成维权和合理的诉求表达,实际上更有可能是一种毁灭性而非建设性的社会改造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