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四月底,一家始祖鸟在西藏林芝巴松措湖南岸正式开业,它的位置海拔三千五百米,窗外便是交相辉映的圣湖和雪山。
不过,让我产生兴趣并不是这家声名远扬的户外店,而是与其联名的品牌——松赞。稍微查看资料就知道,松赞的每一家酒店都位于千米海拔的青藏高原上,有的甚至建在人迹罕至的冰川地带。即便如此,松赞酒店依然火爆到一房难求,是中国野奢酒店的“顶流”选手。
这让我不仅对松赞,也对这一类诞生于高原的品牌产生了兴趣:刻板印象中,高原坐拥独特风景文化的同时物质经济条件欠佳,而奢侈品则是消费社会的宠儿。二者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张力,这些品牌要如何从高原上生长起来?他们在产品打造、品牌内容构建上又有什么独特的方法论?
今天,我们就以两个脱胎于高原的品牌为引,一窥他们背后的故事。

在四千米的高原上,
打开藏地秘境之门
在海拔3700米的松赞拉萨酒店,透过窗户便可以看到坐落在一片碧绿中的布达拉宫,半坡上的绿草和山石形成交错的纹路,如同一块意外掉落在人间的玉石。
无可比拟的窗景,承载着松赞创始人白玛多吉对家乡的执念。二十四年前,白玛多吉听到一位同事如此评价香格里拉:“这么美的地方,住得却这么差。”这让他决心以更有力的方式改变和传播自己的家乡,遂辞去央视纪录片导演的职位,全心投入松赞文旅的建设中。经过多年实践,白玛多吉终于找到了能够承载自己雄心的产品——滇藏环线。他用从丽江到拉萨的多条旅行路线,以及像珍珠般散落其间的松赞酒店串起这片至美景地。
但与众不同的是松赞的酒店选址。比如松赞来古山居建于4200米海拔之上,是整条滇藏线的制高点,酒店镶嵌在悬崖上,推开窗就是冰川和湖泊。

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反常识的做法:以往酒店大都布置在交通易触达的地方,松赞却偏偏将酒店选在偏僻处、让游客千里迢迢赶来。背后蕴藏着怎样的逻辑?
这便要回到松赞的品牌slogan——隐秘之门。以“门”自居,便意味着松赞有沟通和链接的意义。门外是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门内正是不为人知的藏地秘境。松赞将选址思路概括为三点:
第一,松赞的选址不在主道上,为什么让客人奔波到这个地方来?
第二,松赞可以开在别的地方,然后带客人来这里看景点,为什么要让他住在这里?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点,这个村庄是不是需要松赞帮助?
将酒店布置在人们无法到达的山村,使得松赞酒店本身也成为目的地中的一部分。“所有松赞山居和松赞林卡酒店所在的地方,在没有松赞的情况下,是没有可达性的。反过来,我们也通过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景观,让客人体验到很多藏族美景和文化。”

如果说前两点是松赞对景色筛选的高标准,那么第三条思路则是品牌反哺当地的体现。对于白玛多吉来说,“在地品牌”和“可持续”几乎是同义词——如果没有当地人加入品牌建设,如何为客人提供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于是,松赞索性将产品研发权力开放给员工们:管家司机都可以提供项目建议,被采纳之后再按照松赞的标准做提升。
比如松赞的一名藏族司机开主,家住一座带大庭院的藏式传统民居,距离附近的松赞林卡步行只需五分钟。走进宅子,只见老母亲穿着粉红色绣花藏装坐在佛堂前,便宛如看到了一幅油画。于是,旅行线路中藏家宴的体验环节就放在了开主家。游客可以换上藏装、吃传统藏餐、听着藏歌,再一起跳锅庄。对于开主来说,一家人都不用再外出打工,也可以有很不错的固定收入。
有了榜样,其他人也开始动心思。塔城的石磨豆腐、梅里人家的藏式下午茶和手工印制经幡、奔子栏的木碗……这些极富当地特色、但对外地人来说难以发掘的体验,就这样进入了松赞的常规旅行产品。

“这对本地人意味着收入,对松赞的客人来说,则是不加创造的真实的藏地生活体验。”在松赞的体系中,可持续已成为促进品牌吸收在地文化的养料。至今,松赞仍有90%以上员工都为本地人。2013年,松赞员工的年收入就达到了维西县年户均收入的五倍。
到这里,便可以理解松赞的一系列看似奇怪的动作:为什么要在四千米的冰川上建造酒店,为什么不让原住民到更接近市区的地方来、而是请游客就算翻山越岭也要到大山褶皱中去?在地化服务的核心,是保留员工原有的文化身份。因此,不是通过落地城市将只言片语的在地文化“带出去”,而是用一种稍有门槛的方式请人们“走进来”。虽然麻烦,却能尽量保护在地文化的完整性。
去年,松赞与著名户外品牌始祖鸟的联名大秀,便落在香格里拉高山之上。模特们穿着始祖鸟冲锋衣、佩戴藏族服饰,在莽莽高原中不仅毫不违和,而且迸发出一股野性的生命力。
这份藏地文化的包容与深邃,或许正是他们敢于驻守高原的底气。

用一个牦牛绒品牌,
改变一个地区的命运
“在一个偏远贫困的游牧地区开设一个工作坊,培训原本只会放牧的人,让她们为世界上最受推崇的时装公司制作纺织品。”许多年后,金姆雅诗在品牌自传中这样形容她和女儿德清雅诗的事业。这份不经意的调侃,在当时却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
2004年,德清雅诗在母亲的指引下第一次踏上了安多藏区的土地。在对两吨牦牛绒进行实验后,她惊喜地发现这种材料超出预期地柔软、保暖且耐用。就像牦牛的藏语名“Norlha”的含义一样,是“神赐的财富”。

但当地人似乎并不知道这种材料的价值,依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遇到恶劣天气或传染病爆发,牧群就有可能全军覆没。看着许多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已嫁为人妇、过着早出晚归的辛苦生活,看着他们即便拥有高原的赐予、却因缺乏渠道和现代化观念而在基础生计中挣扎,德清雅诗被这种强烈的反差深深触动。
“我意识到这个地方是我可以去改变的,我要对自己做一个承诺,不能轻率地对待他们的人生。”在这个颇显理想主义的念头下,德清雅诗在仁多玛村一呆就是二十年。
为了彻底改善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德清雅诗意识到自己要做的并非一个寻常意义上的品牌,而是一份艰辛且漫长的事业,是“一种可以带来改变的产品, 这个产品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使创作者为之自豪,最终消费者也能珍惜并传给后代。”为此,她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商业模式:一家产销一体的、由自己来把控全产品链的公司。从原料采集到制作,每个环节都要渗透进诺乐的价值观。

于是在2006年,两顶帐篷、几台织布机,和不到十个从柬埔寨、加德满都培训归来的员工,构成了第一间诺乐工坊的全部。对德清雅诗来说,品牌构建的第一个难题是双向的:她既要让更广阔的市场看到牦牛绒织物的价值,也要让擅长编织、掌握牧群资源的当地人相信这份事业有成功的希望。
第一条诺乐牦牛绒围巾在推翻重来了几千次后完成。抚摸着织物细密的经络,德清雅诗越发相信,牦牛绒的价值只能通过纯手工技艺来实现,即便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过程——三十头牦牛的绒毛、细分成十几道的生产工序、整整四天的工期,才能织成一条围巾。特别是在编织经纬线的环节中,稍有误差就要全部重来。
在严苛的要求和工序打磨中,品牌的性格、气质也渐渐清晰起来。“和机器制造不同的是,我们不想做大量相同的东西,只想做特别的款式,每款十到二十件左右就行。”
对产品温度而非数量、传承而非迭代的追求,与奢侈品牌的内核不谋而合。2008年,德清雅诗将牦牛绒产品带去巴黎时装周展示,之后便迅速成为爱马仕、LV、Lanvin等品牌的供应商。2013年,在被更多媒体报道以后,诺乐开始逐渐向品牌转型,并拓展自己的电商渠道。

知名度变大、商品卖的好,对诺乐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解决了现金流问题,并且有能力让员工过上更体面的生活。
2020年初,诺乐在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提到:“共有132名员工在这里工作,110名是仁多玛村本地人,其中67%为女性。”夏天,当地妇女凌晨三点就要起床挤奶,然后收集粪便晒干做成燃料,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而诺乐的出现,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女性员工们不必再忍受风吹日晒,而是像“城里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闲暇时间还可以去参加工坊里的英语、篮球等兴趣班。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带来了稳定的现金流,让女性拥有更多自主权。单亲妈妈可以独立抚养孩子,家中长女也有能力赡养父母。诺乐的员工道吉仁青说:“诺乐的出现,让一部分牧民得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除了对人的关注,诺乐也反哺了这片养育她的草原。诺乐为牧民们提供的就业机会,为草原减少了至少1250头大型牲畜食草量的负担,极大减少了过度放牧对草原生态的破坏。
如今,诺乐工坊已由最初的几顶帐篷,发展为几排整齐的厂房,沉默而坚实地矗立在安多藏区一隅。纪录片《The Norlha Story》记录了她们的日常状态:偌大的房间四角放置着看似古老的纺织机,阳光从中间的玻璃屋顶洒进来,给正在中庭做牦牛绒织物的藏族女工们披上一层白金色的外衣。不久以后,她们手下的产品就会漂洋过海、被送去巴黎时尚大道上的奢侈品店内。


回到开头,金姆雅诗在书中提及的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真的被德清雅诗用二十年时间实现了。诺乐是一家建立在贫困游牧地区的奢侈品品牌,而她更大的价值,应是对当地资源的重新利用、以及对当地人的重新发现。
我试图概括她们之间的关系,却因资料缺乏而无法调动更丰富的语言。因此,在这里引用曾亲身前往诺乐工坊、采访德清雅诗的作者——郭婧雅的一段文字作结尾,或许再合适不过:
“我意识到德清所做的不是推翻旧秩序,这里并未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诺乐更像是原有的枝干上发出的新枝。它所做的,只是重新发现产自当地的廉价原材料的价值,重新赋予手工劳动以尊严,它为那些家里牛羊数量少的牧民、离了婚的妇女、还未出嫁的女儿提供了体面的工作机会。德清的努力,是在这一根新枝上,一点点重塑‘人’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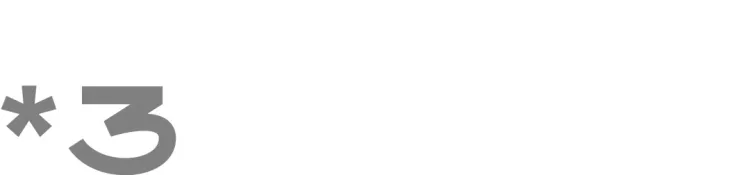
从高原品牌,
看到可持续与在地化融合的可能
如果要总结松赞和诺乐的品牌特征,不外乎两点:在地化、可持续。
这是两个早已不新鲜的标签。自2018年国潮风兴起,消费者就越来越关注在地文化的声音;可持续的风潮更是席卷全球,如今恐怕没有哪家企业不知道ESG营销……而松赞和诺乐的优势在于:他们从根源上打通了在地化与可持续这两个因素,使二者互为条件、互相推动。
为了解决当地就业问题,两个品牌都雇佣当地人做员工,这在前期要付出巨大的时间金钱成本。但正是这一点为他们后期带来了更丰富的在地内容资产,比如松赞旅行中的藏家宴等文化体验,再如诺乐手工艺制作难以比拟的品质。
于是,“可持续”和“在地化”两座看似困难的大山,在这两个诞生于高原的品牌内部形成了巧妙的融合。它们不再是两个需要分别攻克的难题,而是当前者被吃透的时候,后者就会水到渠成地得到答案。

那么如何透彻地实践可持续?这实在是一个无法用商业回答的问题,二十年前从央视辞职的白玛多吉、从纽约飞到青藏高原的德清雅诗也无法回答。就像当初德清的朋友们无法理解她为何要放弃优渥的生活、远赴高原研究一种叫牦牛绒的东西,更无法理解她为何要留在彼时穷困的仁多玛村。若要追溯到最初,做可持续这件事或多或少是带了一些理想成分。因为它不是临时起意、要争夺眼球,它不带来短期利润、甚至会带来亏损,而是一份长期主义的、能改变当地人生活的事业。
说到底,可持续与在地化拥有相通的基因。他们共同的铆点,就是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关注和热爱。
相较之下,近年有许多奢牌想要通过在地化营销占领更多中国市场,却总因肤浅、奇怪的设计引来群嘲。表面上似乎是对中国消费者示好,本质上还是不在乎中国文化,才会想要通过堆砌符号来博得好感。
而松赞和诺乐,让我们看到了品牌在地化更高的形态:用品牌发展带动当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在地文化也会自然渗透进品牌内容。比起空洞的物质符号,他们的坚守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