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来才知道国庆长假我们都去了泉州,一个是回家乡,一个是去旅行,然后分别回到上海和深圳,完成这场对话。
《皮囊》的畅销,让你在聊到书写泉州的作家时,很容易第一时间想到蔡崇达。伸开触角却发现他几乎没有什么公开的联系方式,恰好此时看到他睽违八年之后推出了第二本著作《命运》。好巧。
蔡崇达愿意接受采访,我想很大部分原因是我们邀请函里提到的这一期的城市群像专题想“聊聊泉州”。
“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这感慨往往夹带着一些辛酸。但是,回头看一下,出生在泉州的某个小镇,出生在任何乡村和街巷,都可以是一种天赋和祝福。当原始积累的天然壁垒不再是唯一执念,家乡的可爱之处也就愈加清晰可见,而只有当我们都能找回自己的家乡,家乡也才能不再以北上广为唯一坐标。
泉州去年申遗成功,成为近两年的热门目的地,但还不算太红,不过去过的人都觉得“很有意思”,这里面的“意思”,也许借由它近些年的“代言人”,可以窥得一二。

#一个作家的第二本书
TOPYS:距离您的上一本书《皮囊》已经8年,《命运》这本书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素材累积和实际写作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蔡崇达:作为一个作家,《皮囊》让我挖到了一个精神的富矿区,但是否应该再次去挖掘,这个问题追了我好多年。
我常说作家的第二本书往往是能够见真章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作家的第一本书就是他/她最被认可的作品,因为第一本书往往是一个写作者在他的感受和思考到达某一种状态的爆发,是一种应激状态的喷发,第二本书如果要超越第一本书,作家就要理解并且吞下内心那些母题,然后找到一种有秩序、更深入的表达方式。如果第二本书能超过第一本书,往往这个作家的写作格局就会打开,写作方法会更加多元和轻盈。

《皮囊》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发行了各个语种的版本,韩国版发行的时候,文学评论家李金格说,他认为《皮囊》的畅销,是因为作者试图用古代中国的智慧呼应和治愈当下的中国。这句话给我的触动非常大。
我后来意识到,《皮囊》的畅销,其实是闽南文化的畅销,而闽南文化的畅销其实是传统中原文化的畅销。泉州历史上,每次中原发生战乱,士大夫家族就衣冠南渡,带过来的不仅是人,实际上是一套精神秩序,一套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把这些文化碎片带到海边这个地方储存起来,沉积在这边。所以你会发现泉州的很多习俗是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有的是东晋时期的习俗,尊神事鬼,有些是唐朝的、宋朝的,这些碎片最终又化为日常生活。我经常说的大俗和大雅,一些看似非常土非常俗的俚语当中、习俗背后,都有非常雅的对生命的提炼和认知。
现在是一个比较辛苦的时代,用我的话来说很多人的精神是裸奔的,我觉得用我们老祖宗和自己命运相处的这些心灵秩序,来陪同每个人去面对当下这种巨大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命运》这本书的目录有点像招魂仪式,其实是在召回传统文化、内心魂魄,来陪伴我们自己。

整个写作没有太多所谓积累素材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探索的过程。整本书写了大概三年,但是有一年半花在开篇上,开篇我写了27遍,每一遍都写了七八千字到1万多字。它是我的生命历程里的部分,但是困难的是进入的方法。
TOPYS:我们所说的素材积累可能是渗透在生活里的,但是本身沉浸在这个环境里的人,有时候是很难抽离出来去看待和观察的?
蔡崇达:其实每个人都是被时代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人与自我之间的以及自我这五重关系塑造出来的。所以你只需要不断地感知自己,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样子倒过来翻译,当你用那种眼睛去看一个人的话,你就可以通过一个人写出那个时代来。
很多文学评论家都提到说《命运》很大胆地虚化历史背景而关注人,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当下更准确的表达方式,把焦点更多放在人心,而不是放在世界。
TOPYS:如果自己来评论的话,您会觉得这第二本书超越了《皮囊》吗?
蔡崇达:写作很多时候重要的是准确和合适。我大概每隔半年会读一遍《皮囊》,我现在很笃定,《皮囊》的表达方式是准确的,它可能会显得有些笨拙,某些地方因为情感过于浓烈,甚至有声音嘶哑的感觉。但这何尝不就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最准确的语调和最准确的样子?如果你让我现在重写,它会在技法上更完善,但事实上它更不准确了。
我会觉得30岁时候写的《皮囊》达到了它该有的情感的烈度,真诚度和细腻度,然后到现在40岁的《命运》,开始会有一些更深入的探讨,感性理性交织的表达。我觉得我都尽力了,如果说有超越,那可能是成长历程的超越。
《皮囊》是一本成长之书,里面的一个个碎片,是电光火石之间的应激反应,《命运》有体系有前因后果有流淌感,其实是两个不同调性的东西。

TOPYS:我读《皮囊》有类似的感受,有时候在某种状态下读会觉得很能共情,但是如果换一个场景,又确实有您提到的情感浓度过高,甚至有点尴尬的感觉。所以您刚才提到30岁写皮囊的状态,我觉得是很准确的。这种“情感过于浓烈”的状态其实在很多写作者身上都会有,可能刚开始写的时候情感非常奔放和流畅,但是如果回去修改细节的话,可能会默默把这些情绪表达也往回收了。
蔡崇达:有没有过度表达,我觉得判断标准还在是否真诚。如果是你内心试图克制,又还是憋不住的那种情感的话,这种冲撞体现在你的文字里,我觉得是好的,也是珍贵的。但如果只是情感的泛滥,那种东西你再读会觉得很尴尬,你也知道不是特别真诚和有力量。
TOPYS:您的职业经历很长时间其实都是在北上广一线城市,之前的写作可能也更聚焦在城市或者时尚领域。您是怎样把书写泉州文化认定为个人写作的命题呢?
蔡崇达:应该说这十几年的媒体工作,让我感知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灵魂,这其实是一个作家的根本积累。
不止一个作家经常跟我说,好羡慕你老蔡,你是个拥有家乡的作家。实际上在我看来作家就必须拥有家乡,因为家乡是塑造你灵魂的最根本的地方。你只有理解了、拥有了家乡,你才算拥有对自我的相对完整的认知。你会发现其实几乎所有作家在某个时期都必然精神上要回归家乡的。
#根系、文化和精神秩序这个母题
TOPYS:刚才您提到说有三年级的小朋友读《皮囊》,其实死亡教育这个问题古今中外都存在。很多人对于《命运》的开篇感到很震撼,关于死亡的讨论和交流在中国往往是一个禁忌话题。老人可能已经很高龄,身体很不好了,但是家人只会说你没事,用这种方式去安慰他,但事实上没有人帮助他们去面对。
蔡崇达: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也在琢磨啊,我们老家一是节日特别多,二是公共事务特别多,除了对神明、对老祖宗的祭祀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个人的每个重大的生命的节点,从怀孕到一个人出生、满月、成年、结婚、又有孩子,到一个人去世,几乎所有人都要参与。我现在已经在外面工作了,还经常会有人来告诉我,你哪个亲戚怎样了,你应该回来,如果回不来,那么你应该要做ABCD各种事情。每个重大节点,那个人都不是孤独的,宗族都必然要有仪式和方案提供给你,让很多人参与进来。这倒过来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早早演练必经的人生历程,包括死亡,死亡真的是我们最经常要经历的东西。
如果你细琢磨,同一套仪式其实是由不同朝代的习俗构成的,但是他们相安无事地放在这地方,可能人生太苦了,所以所有的解决方案、所有的心理秩序,只要不矛盾,都可以用,拼命用。所以我们老家不止面对死亡,面对成年、面对各种生病,都有满满当当的仪式。


我这次回老家,有一天大家喝酒,有人问说,如果再投胎一次,你们会想选哪里?然后真的在座都异口同说还是闽南。本质上我一直觉得身为闽南人幸福的一点是它的精神秩序是如此地完备和丰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各种坎、面对生老病死,有各种世俗的礼仪和精神方面的体系去拥抱你,这是我觉得泉州挺可贵的部分。
TOPYS:如果不是在特定的某个文化里面,很多年轻人其实对于所谓的宗族家族是偏排斥的,会觉得好像比较繁琐、不明所以。前段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在开玩笑说泉州的富豪联姻图,这是不是其实跟当地的一些宗族、家族意识也有关系。
蔡崇达:我在书里写道,闽南的女人嫁过去的话,接管的不只是家里的财政或者说生活,她还要接管一整个家族的精神世界。太主公的忌日是什么时候,我们宗族的大的活动是什么,过年过节家族一定要组织有钱人去看望没钱的人,谁生病了要整个家族去捐钱治病等等。
其实你到闽南的乡镇去走走,会发现经常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父母一起拜拜,各种习俗主要都是靠女性之间口口相传传下来的。闽南男性的角色是打鱼捕鱼、做生意,对外去考虑现实的生活要怎么样进行下去,而闽南的女性掌管的是精神世界。都说闽南的嫁妆很多,其实那不是嫁妆,是提早把女儿的家产分给她了。比如说女方嫁妆100万,男方再拿出100万的聘金,可能已经调动他们家庭里的大部分钱了,就什么都不用讲,交给她来掌控家庭的财政权了,很快地建立了这个角色。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女性如果嫁过来,被欺负了,跑回娘家了,娘家是有权利过来把男方家的房子给拆掉的。
刚才讲到的那个你可以说是富豪联姻,但实际上闽南的男生很多都会和闽南的女性结婚,有时候是因为基于共同的文化,但凡有一个人不懂,这个习俗就会继承不下去,甚至变成冲突。
#《命运》背后的人
TOPYS:闽南文化的书写仍然会有一些理解上的门槛,它可能是文字表述上的,比如闽南方言怎么转换成书面文字,它也可能是观念上的冲突。
蔡崇达:《命运》出来之后,我记得有一个评论说,“读起来特别有异域风情,但是又觉得莫名的熟悉。”其实这就对了。
写文学抵达人心,这句话很多人说过,但所谓的抵达人心到底是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十三四岁时总会知道一本书叫《少年维特之烦恼》,虽然你不一定读,十七八岁,你总会知道一本书叫《在路上》,虽然你不一定读完它。为什么会有经典文学存在?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人性有很多共通的命题,但是人其实很难理解自己,更不要说表达自己。当一个写作者把自己内心深处本来很难理解、很难表达的部分表达出来了,很多读者就可以进入你的表达。
所以其实我对自己写作的期待不是畅销书,而是希望有机会长销,因为长销书意味着我是你内心深处的命题的表达者、陪伴人。
TOPYS:好像闽南的写作中总难免有一些悲情的故事。
蔡崇达:它是苦的。
其实《命运》只是讲了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生命的诸多挑战,生老病死等等,苦是生命的常态,但苦有时候可能是生命的获得。
我说一下我真实的故事。我一直觉得这么多年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我父亲当时做完一个大手术,心脏瓣膜的手术,我们无法回老家过年,就在重症病房里,我父亲还在吊瓶,但是他感觉外面都很热闹,在放烟花,他就说要不我们来打牌,输了就刮鼻子,然后我们一家四口就在病房里打牌。它很苦对吧?但对我来说,在这么苦的时候,我父亲在最困难、人生最无力的时候还在想着照顾我们,何尝不是最幸福的时刻。
其实《命运》这本书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内心是很有力量的。如果你问我阿太的一生,我相信她不会跟你说是苦的一生,她觉得她一生过得很好。其实当一个老人已经趟过命运的诸多河流,还能笑眯眯地慈爱地看着你,告诉你这世界很好,其实她已经消化完这世间不好的部分,然后尽可能地留住和珍惜了这世界好的部分了。
我阿太就是好好的活着,活得很好的一个人。
TOPYS:不管是谁成就谁,从《皮囊》到《命运》都是知名度非常高,泉州文化也因此可能被更多人认识到。在宗族文化这么浓厚的地方,您本人会不会有点承担像乡绅的这种责任在做事情?
蔡崇达:我从一出生就深受闽南文化的恩惠,它让我内心在最困难和惶惑的时候,都有一种很坚定的力量,所以我很希望把这些恩惠表达出来。
泉州的精神体系真的是有一个根系,比如说我们每60年就一大祭,全世界从宗祠出去的人都要回来,要不他就没有根了。我们的族谱上你一翻开你就知道自己从哪来,后面长出的又是怎样的人,你就看得到你从哪来、到哪去。泉州有七八百万的居民,但是号称有三千万人,因为虽然泉州很多人已经成为华人华侨,但是其实他跟我一样经常回来。你到泉州去,会发现所有的重要的公共设施都有人捐建,大到机场小到学校实验仪器,像我捐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也是类似的,因为我们的精神根系还跟这里相连着。

倒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乡绅,应该说这几年,我在泉州简直是团宠,可能以前泉州有企业家,但在当下我很幸运能成为表达家乡的人。
其实写完这本书之后我是住院的,本来以为回老家是休息,结果通过各个路径找我要签名的书,签了应该有5000本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誉,就是跟这片血脉相连的土地获得这么深的共鸣。那天我路过小学,有人说那不是蔡崇达吗?虽然我已经胖了20斤,但他们认出我了。
我回老家,没有所谓的包袱,穿着拖鞋,排队去买小吃,然后去庙里坐一坐,去寺庙的时候,有人就说你又来了,我看你书里写关帝庙,你又来关帝庙了,然后住持也认得我。我只能说荣幸,何德何能,铺天盖地的那种全方面的回响。
TOPYS:《命运》算是长篇小说,《皮囊》定义是非虚构,里面涉及到的人物很多,我们知道很多作家写非虚构或者身边人的故事,是会产生一些后果的。《皮囊》里面写到的一些人知道这本书,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
蔡崇达:其实当时《皮囊》在定义到底是不是非虚构的时候挣扎过很久,写他人的故事我后来还是做了一些修饰和保护了,但是当事人能看出来是写他。比如说其中一篇里的主人公,出完《皮囊》之后,我有段时间也很担心要怎么去跟他相处,但得到的反馈也是我比较意外的。他听说我回来了,有一天突然来敲我家的门,然后他也没干嘛,就说我想看看你最近怎么样,你还在写东西真好,然后坐了一下,就说一句加油,突然就要走,跟我说“我也会加油的”,就走了。
我后来是这么理解的,我写《皮囊》的时候,不是在评判谁,而是在拼命地试图看见谁理解谁,即使可能有诸多的困难和不堪,但其实人人都是渴望被理解的。这种发心骗不了人,你是为了猎奇,还是为了故意去卖他的人生,还是想要理解他,其实人人心中都是敏感的。
《命运》这本书是一本虚构小说,虽然有原型。我们老家真的有个医生叫青山,跟小说里的青山医生是无关的,但他就会到处跟别人讲,我就是青山医生,还特意叫一个亲戚跟我说感谢我写了他,明明里面写的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故事了(笑)。他们觉得还是写出了我们这个地方人的精气神,所以大家还是想认领其中的角色,特别好玩。
#泉州将成为一座疗愈之城吗
TOPYS:可能通过这两本书,大家对于闽南文化会有很更底层的感悟,但是如果从更面上来说,您会觉得应该怎样通过文旅的方式让大家更了解泉州的文化,或者说怎么向年轻人介绍泉州?我国庆刚刚从泉州回来,很有意思,但是我发现小朋友或者说更年轻一点的人,对于这些的感受力还是会有一些隔阂。
蔡崇达:对,很多人都觉得泉州很“吃亏”,泉州真的很有东西,但是又很难表达。其实泉州试图用过很多方式形容自己,“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中国”,指的是宋元时期的世界第一大港,“世界宗教历史博物馆”,确实泉州历史上的宗教融合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还有我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里后来经常被引用的“半城烟火半城仙”,它烟火气很重,但是又很神性,用我的说法“住着最神性的世俗也住着最世俗的神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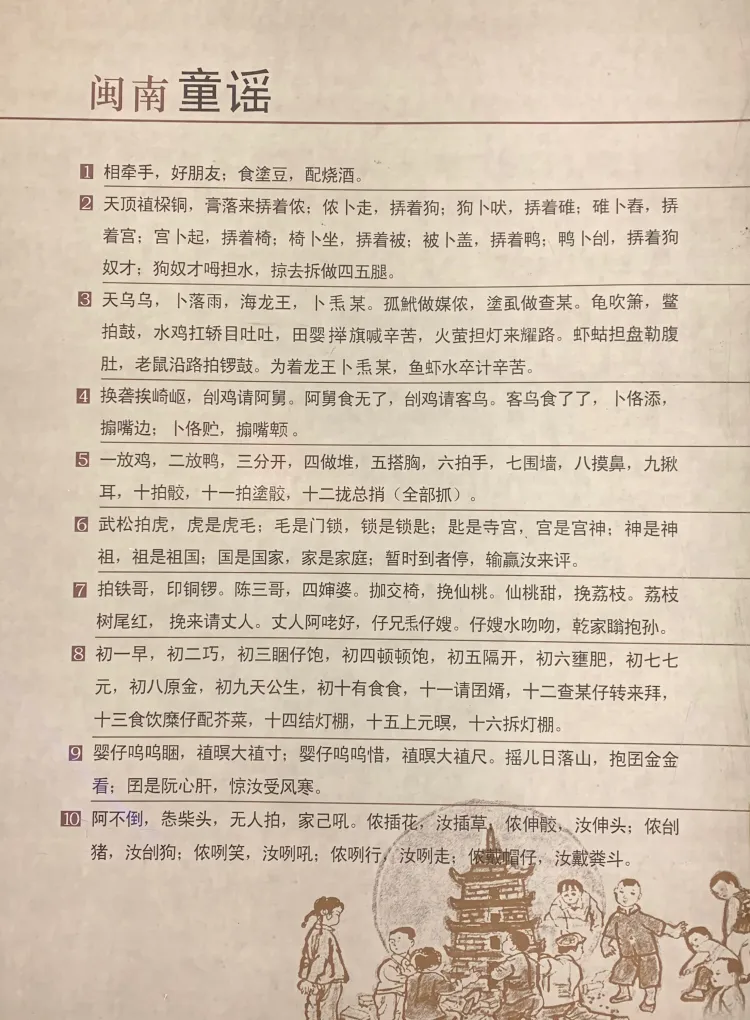
其实我前几天也在泉州,又跟宣传部的人在聊,泉州为什么这么难以被表达呢?我突然间想明白了,泉州本身是世界遗产城市,但在我看来,更可贵的是它人文的、内心纹路的部分。我会建议做更多的具体导引,你想内心获得某种陪伴或疗愈或某种安定,有一个详细的指引地图让你去感受。因为泉州那些古迹都还活着,比如说为什么要吃这顿饭,这顿饭又为什么这么做?一个个神明,一道道菜一个个仪式,都是一个个心灵秩序的具象化的结果。
所以我现在会建议泉州应该从内心体验上来表达,让大众更好体验一点。泉州其实有很重要的当下性,能真真正正治愈人、陪伴人,人内心深处那种惶恐不安,只要你感觉有某种秩序或某个人在那陪伴,心理压舱石是很重要的。只要把这个部分表达得再清晰一点,我相信泉州对大众来说就会是一座特别有幸福感的城市了。




